時間:2023-06-18 10:45:52
開篇:寫作不僅是一種記錄,更是一種創(chuàng)造,它讓我們能夠捕捉那些稍縱即逝的靈感,將它們永久地定格在紙上。下面是小編精心整理的12篇殷商文化的主要特點,希望這些內(nèi)容能成為您創(chuàng)作過程中的良師益友,陪伴您不斷探索和進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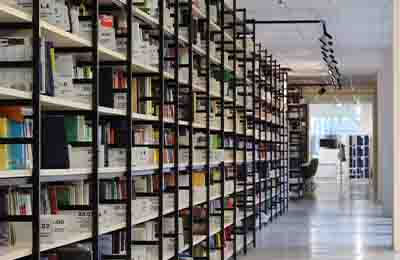
關鍵詞:中國;字形;演變
語言文字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在漫長的歷史發(fā)展中逐漸形成自身的發(fā)展規(guī)律,并在長時間的變遷中逐漸正規(guī)化,通用化。而中國的漢字正是在這種發(fā)展中逐漸正統(tǒng)化,衍生出了當代的漢字造型。總體而言,中國漢字的形成可以大致歸結(jié)為以下階段:商代之前一直屬于文字的起源階段,當時還沒有規(guī)定全國統(tǒng)一的文字字體,通常是人們約定俗成下的文字造型,殷商甲骨文為成熟期。就此以后,漢字就開始了其漫長的衍化歷程,而其中最為重要的就是漢代,隸書取代小篆成為主要字體,中國文字的發(fā)展就真正脫離了古文字階段進入到新的發(fā)展時期,在宋朝出版的相關書籍中漢字被重新稱之為宋體字,并逐漸形成了當今人們廣泛使用的仿宋體,也為當前中國的漢字造型發(fā)展做出了重要貢獻。漢字作為當前世界上使用時間最久、空間最廣、使用人數(shù)最多的文字之一,其的發(fā)展過程不僅推動了中華本民族文化的發(fā)展,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中華文化的傳播,同時也對世界文化的發(fā)展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無論是最早的甲骨文還是當前被廣泛使用的宋體,雖然在寫法上已經(jīng)有了很大的變化,但是漢字真正的內(nèi)涵卻從未發(fā)生改變,仍然將表意作為主要特點,而這也是中華文字的獨特之處所在。筆者希望通過對于當前中國漢字字形演變的研究,對當前中國文字字形進行簡單的梳理,不僅有利于加深筆者對此的理解,同時也有利于當前中華文化的傳播。本文將分為古文字和今文字兩個階段進行樹立。
1 古文字階段
古文字階段包括從殷商時期的甲骨文直至秦代的小篆這一歷史時期。其間流行的主要書體包括甲古文、金文和篆書。這一階段的文字主要仍然以圖畫的方式進行字意的表達,還沒有真正的形成字體中的筆畫,因而在這一階段的漢字上呈現(xiàn)出顯著的圖案美特點。
1、甲骨文
甲骨文顧名思義,是古刻在龜甲和獸骨上的文字。這也是中國目前已知的最早出現(xiàn)的文字,其最初出土于河南安陽小屯村的殷墟,所以又稱甲骨文為“殷墟文字”。這些文字的出現(xiàn)有著特殊的效用,并不是為了便利人民的生活而被創(chuàng)造,主要是為了滿足殷商王朝的宗教祭祀和占卜的需求,因而主要出現(xiàn)在用于占卜的龜殼上。甲骨文大部分為契刻,也有少量墨書;有直接契刻的,也有先書后刻的。因大多是契刻的,故又稱“契文”。甲骨文大部分為殷商遺物,其的出現(xiàn)標識著中國開始出現(xiàn)了記錄的工具,中國的文字發(fā)展從此開始。
2、金文
金文,主要是指古代鑄或刻在青銅器上的文字,通常專指商、周、秦、漢時期的銘文。因鐘和鼎是古代的重器,言鐘鼎可以概括其余的銅器,所以又稱為“鐘鼎文”。經(jīng)過歷史學家的研究發(fā)現(xiàn),金文的出現(xiàn)時間晚于甲骨文,并承擔了從甲骨文到篆書的過渡作用。但是,金文并未像甲骨文一樣被廣為發(fā)掘,從當前發(fā)現(xiàn)的數(shù)量來看,仍然較少,其主要在商周時代被廣泛使用,而周代之后的銘文,字體逐漸過渡到篆書。
3、篆書
“篆書”又稱“篆文”,在傳統(tǒng)意義上,被分為“大篆”和“小篆”。“大篆”先于“小篆”而存在,主要是指秦統(tǒng)一文字之前在秦國通行的字體。就當今來說,我們能從《說文解字》和各種鐘鼎彝器上看到大篆的蹤跡。
而“小篆”是在“史籀大篆”的基礎上形成的,其主要目的仍然在于通過文字的統(tǒng)一促進政治統(tǒng)一的實現(xiàn)。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tǒng)一六國,結(jié)束了春秋戰(zhàn)國時期諸侯紛爭割據(jù)的時代,開始了中國統(tǒng)一中央集權(quán)國家的建立。政治上的高度統(tǒng)一,必然要求文化上的大一統(tǒng),要求文字的統(tǒng)一,于是,小篆便從這一時候孕育而出,成為了當時全國上下通用的文字,也在一定程度上便利了人們的日常生活。小篆相比于大篆來說,通過對于字形的簡化能夠更加適應日常生活的需要,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漢字的數(shù)量,促進了語言的準確表達。
從甲骨文、金文到大篆,從大篆到小篆的文字變革,古文字時期的變革在中國漢字史上具有不可忽略的意義,占有重要地位。
2 今文字階段
4、隸書
隸書發(fā)端于周末,并在很大程度上實現(xiàn)了字形的變革,縱然當時的篆書實現(xiàn)了人們?nèi)粘J褂梦淖值囊?guī)范,但是由于寫作的復雜性,因而也帶有無法避免的復雜性,隸書在此基礎上繼續(xù)進行簡化,具有簡省盤曲、筆道改圓為方的顯著特點。且字形不像篆書那樣長方形,而呈扁方形。這種從隸書到篆書的巨大轉(zhuǎn)變,不僅是時展的必然要求,同時也是滿足人們?nèi)粘I畎l(fā)展的需要。而從隸書中,我們可以看到,字形本身已然有了筆畫的構(gòu)成,字形開始呈現(xiàn)出一定的規(guī)律性。
關于隸書的形成,歷史上宗說紛紜,當前學界也沒有統(tǒng)一的結(jié)論。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隸書的形成是一個逐漸形成的過程,在春秋戰(zhàn)國時期,一些文字已然開始呈現(xiàn)出隸書的形態(tài),而同時篆書的復雜化也對文字的發(fā)展提出了新的需求,趨捷趨簡是文字書寫的大趨勢。而隸書本身的創(chuàng)造也是歷史發(fā)展的結(jié)果,是廣大漢字使用者造就了隸書這一書體,并在隨后的生活實踐中被廣泛使用。而就當前的隸書來說,以《云夢睡虎地泰簡》為代表,我們已然可以看出從篆書到隸書的顯要轉(zhuǎn)變,從字形上可以發(fā)現(xiàn),它已經(jīng)擺脫了篆書用筆均勻圓轉(zhuǎn)的特點,變成了橫直的筆勢,而這也進一步促進了篆書到隸書的成功過渡。到了漢代,隸書代替篆書而成為標準書體,字形扁平就成為隸書的顯著特點。從隸書開始,形體從線條轉(zhuǎn)為筆畫,標志著漢字由“古文字”階段跨入了“今文字”階段。
5、楷書
隸書對篆書來講,已然實現(xiàn)了字形上的成功轉(zhuǎn)變,是漢字發(fā)展史上的―大飛躍,也對現(xiàn)今文字的發(fā)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雖然隸書在字形上已經(jīng)很大程度上實現(xiàn)了簡化,但是“蠶頭燕尾”、一波三折的要求也仍然并不適合人們?nèi)粘I钪械挠涗浐蜁鴮憽TS慎《說文?敘》中所說“漢興有草書”,就是在隸書基礎上實現(xiàn)的字體的另一種衍化,因其草率而就,故稱為“草書”。草書雖書寫快捷,但書寫草率,并且由于個體的差異無法形成y一的標準,甚至在辨認上也存在一定的難度,僅僅具有觀賞性,在這種情況下,楷書應運而生。所謂“楷書”,意思就是可以作為典范楷模的書體。
楷書萌芽于東漢末期,并在長期的歷史發(fā)展逐漸成熟。在三國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書體,仍然可以體現(xiàn)出半隸半楷的特征,如三國吳鳳凰元年(公元272年)的《谷朗碑》等,都能夠看出從隸書到楷書的過渡階段。而到了隋唐,楷書正式脫離了隸書,形成了一種正式的字體。楷書形體方正,極具觀賞性的同時也頗具實用性色彩。這種橫平豎直的方塊形結(jié)構(gòu),也被當今的中國字形所繼承,成為了中國漢字最為顯著的特點。
參考文獻
[1]許慎.說文解字[M].暢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2014.
[2]李梵.漢字的故事[M].暢西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
關鍵詞:思想品德教育;中學美術教育;德與才
教育的目的在于促進人的全面發(fā)展,提升人的能力,共同推動社會的進步。百年大計,教育為本,教育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中具有非凡的意義。在人的教育中,道德素質(zhì)應該排在首位,也必須排在首位,如果沒有德行,那么他的能力再強,對社會來說,他也是一個無用甚至是一個有害的人。“師者,傳道授業(yè)解惑也。”在這里,我認為“道”不僅僅是學術上的道,更重要的是思想上的道。然而在傳統(tǒng)的美術教學中,教師往往只注重學生美術技能的學習,忽視了學生思想道德的教育。這也是新課程改革下,強調(diào)美術教學中對學生思想品德教育的重要原因。那么,在美術教育中如何貫穿思想教育,根據(jù)美術教學以欣賞美、表現(xiàn)美和創(chuàng)造美的主要特點,在美術教學中,貫穿思想品德教育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展開。
一、欣賞評述課中的思想教育
欣賞評述課,主要是通過中外歷代的美術作品的簡介和欣賞評述,來提高學生的審美能力。在欣賞評述課中,可以讓學生了解中外歷史上一些代表性的作品,通過初步認識,引導學生去理解、領悟和感受美術作品的魅力。
在中學美術欣賞評述教學中,有大量中國歷代以來優(yōu)秀的工藝美術作品。比如石器時代的陶器,殷商時期的青銅器,各種壁畫、帛畫、版畫。在這些作品中,有相當多的作品中蘊含著愛國之情,是進行愛國教育的良好素材。教師在備課時,要意識到這些作品中包含的思想情感,進而深挖教材,揭示教材的內(nèi)在思想內(nèi)容。在對藝術作品進行賞析的時候,首先要介紹作品的創(chuàng)作背景、思想內(nèi)容和藝術形式,在此基礎上,對學生進行思想教育,分析藝術手法的體現(xiàn)和運用。比如,湘教版七年級第一冊中的《梅竹精神》和八年級第二冊《詩情畫意》兩個單元的中國畫課。在學習元代王冕的《墨梅圖》時,要注意到畫上的題花詩“不要人夸好顏色,只留清氣滿乾坤”,這句詩表現(xiàn)了畫家的高尚氣節(jié)和不與當時統(tǒng)治者同流合污的愛國情懷。再如,清代畫家鄭燮的《竹石圖》,“咬定青山不放松,扎根原在亂巖中。千磨萬擊還堅韌,任爾東西南北風。”這首詩表現(xiàn)了畫家的剛毅不屈,以竹子自喻來表明自己的人生態(tài)度。中國畫是寫意畫的代表作,通過托物和借物來表現(xiàn)自己的人生態(tài)度和理想。通過對這些作品的賞析來了解中國文人的思想情感,以作品中蘊含的情感來影響學生,進而達到思想教育的目的。
欣賞教學也可以分為多種形式進行,如結(jié)合課本上的圖片和掛圖以及史料典故來分析討論,利用多媒體課件展示所講的內(nèi)容,也可以適當?shù)亟M織學生參觀博物館和畫展。運用多種教學手段對學生進行思想引導,培養(yǎng)學生的欣賞能力和愛國情感。
二、造型表現(xiàn)課教學中的思想教育
造型表現(xiàn)課也就是技法課教學,主要是通過美術作品的臨摹、寫生與造型表現(xiàn)等課程的實踐,使學生了解和初步掌握美術教學的主要特征和技能技法。在臨摹作品中,感受藝術品創(chuàng)作的思想文化,培養(yǎng)學生對美術的興趣和愛好,培養(yǎng)繼承發(fā)揚民族文化的思想情感和良好的審美觀。中學美術教學中,安排學生進行臨摹和寫生,這是對學生進行思想教育的一個重要機會。在課業(yè)實踐中,可以通過學習中國繪畫技法來滲透思想教育。中國畫在材料、題材和技法上都具有鮮明的民族特點,在進行繪畫作品臨摹時,可以進一步了解中國畫的藝術特征。比如,在對某一作品臨摹或某一實景寫生時,教師可以圍繞作品的外在形式,結(jié)合直觀的演示給學生講解中國繪畫的藝術特色和獨特的技法運用。中國繪畫注重寫意性,因此,教師在講解時,可以突出繪畫作品所表現(xiàn)的本質(zhì)意義,通過形式的塑造來表現(xiàn)自己的情感。中國繪畫講究形式美,以線條塑性為主,重視筆墨的勾勒;構(gòu)圖不受時空的限制,不受焦點的約束,同時也注重畫幅留白的運用。中國的繪畫強調(diào)文字、書法的有機結(jié)合,在作品的創(chuàng)作上、表現(xiàn)形式上都具有它獨特的個性。教師注重這些講解,學生可以對中國繪畫有一個更深刻的認識,從藝術的角度來加深理解,掌握傳統(tǒng)繪畫的技巧。通過中國繪畫的魅力來感染學生,引導學生,進而對其進行思想教育。素描是一門枯燥的基礎課程,學生很容易產(chǎn)生厭倦的情緒。因此,在學習之余可以理解作品背后的故事,來調(diào)節(jié)學習的氣氛。
三、削弱“重理性”的道德觀念的灌輸,增強“情感性”教育
提起思想教育,我們會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來約束學生,用道德的高標準來要求學生。但是通常這種說教會引起學生的反感,因此,在美術教學中貫穿思想教育,不能以重理性的道德觀念來教育學生,而應采取柔和的手段來進行情感教育。
在教學前,教師要注意對素材整理和分析。教師可以搜集山石、樹木、花草等一些實物,讓學生欣賞這些作品。觀察畫家是如何認識、描述這些事物的,了解國畫的基本精神和要求。在隨堂練習中,教師要尊重學生自己的審美感知和對事物的認知,讓他們根據(jù)課堂上的欣賞和記憶大膽地表現(xiàn)山石、樹木、花草的形象,讓繪畫貼近學生,同時拉近師生之間的距離。教師要在觀察學生練習中了解學生的心態(tài),運用多種教學手段,引起學生的情感體驗。
在實際教學中,通過對作品的賞析、模仿來引起學生的情感共鳴,從情感上進行思想教育。比如說:在學習七年級第二冊第四課《中國結(jié)》的時候,可以讓學生自己收集中國結(jié)的作品,讓學生自己來講述中國結(jié)的產(chǎn)生和發(fā)展,從中國結(jié)背后的故事來了解它的寓意,從而感受祖國情懷,了解歷代學者文人的中國情結(jié)。學習山水畫家王希孟的作品《千里江山圖》時,教師可以先讓學生觀賞之后說出自己的感受,然后再講述作品表達的意境和運用的繪畫技巧。讓學生在體味中國山水畫的藝術表現(xiàn)魅力時,感受中國精神的偉大。了解國畫與西方繪畫的不同,在欣賞中國繪畫和西方繪畫時,體驗兩種繪畫的藝術魅力,進而在情感方面激起學生的波瀾。
美無處不在,引申到思想教育上也可以說是教育無處不在。在重視美育的同時,也應加強思想道德的教育。在美術教學中要貫穿思想教育,要深入地研究教材,體現(xiàn)教學的層次性,重視情感的激發(fā),真實地提高教學的效果和思想教育的實效。在社會實踐中體會真、善、美,讓學生體驗祖國山河的自然美,激發(fā)新一代學生為祖國奮斗的步伐。
參考文獻:
我們先分析漢語的基本特點。
一般的拼音語言,只有元音與輔音兩個結(jié)構(gòu)要素,聲調(diào)(升調(diào)、降調(diào))只區(qū)別語氣,不區(qū)別意義,因而不是拼音語言的結(jié)構(gòu)要素。而漢語則不同,聲調(diào)起著區(qū)別意義的作用,故漢語語音由聲母、韻母、聲調(diào)三個要素構(gòu)成。如果我們把英語等拼音語言稱為二維結(jié)構(gòu),那么漢語語音就是三維結(jié)構(gòu)。
人類的發(fā)音器官能夠發(fā)出各種各樣不同的音。就語音單位而言,幾乎具有無限的可能性,或者起碼是一個龐大的數(shù)字,但每一個民族用于社會交際的能夠區(qū)別意義的音位卻少得多,這是根據(jù)人類的交流需要而決定的。人類語言只需要不多的音位,就可以構(gòu)成無數(shù)有意義的話語。
從歷史發(fā)展來說,“能指”和“所指”在約定俗成的任意性這一表層現(xiàn)象的深處,有著相當深刻的內(nèi)在聯(lián)系。這種聯(lián)系受到各民族物質(zhì)生產(chǎn)發(fā)展的一般水平和語言發(fā)展水平的雙重制約。就人類語言的發(fā)源處來說,初民不可能也無須選擇很多的音節(jié)來表達一些簡單的概念。但是,隨著生產(chǎn)實踐和社會生活的發(fā)展,有許多新的概念需要表達,原先的音節(jié)不能滿足需要,他們必須尋覓新的途徑。增加音節(jié)是一個最簡單的有效途徑,西方的一些語言就走了這一道路。英語中的音節(jié)就有一萬多個。但也還有另外一個聰明的方法,即在原有的音節(jié)上標出不同的聲調(diào),以此代表不同的概念,這同樣可以起到與增加音節(jié)相等的作用。漢語就走了這一條道路,它只選擇了400多個基本音節(jié)就能夠滿足高度文明的漢民族的各種概念表達的需要。采取增加音節(jié)的線性展開的方式和運用聲調(diào)向中心聚斂的三維方式來解決語音的發(fā)展問題具有同等的有效性。于是,漢語與西方拼音語言的根本性區(qū)別(即拼音語言是用二維——元音和輔音——來表達的,而漢語是用三維——聲母、韻母和聲調(diào)——來表達)就形成了。當然這兩條道路也不是絕對的互不相涉,而是起著部分的互補作用。漢語在發(fā)展中,由單音節(jié)詞為主到雙音節(jié)詞為主,且近代以來,由于文化交流的增多,外來語的翻譯常用多音節(jié)詞來表達,這使?jié)h語的詞匯中多音節(jié)詞的比例也有所擴大。拼音語言也有不用增加音節(jié)而只是改變詞的重讀音節(jié)的方式來區(qū)別意義,這又與漢語所走的道路有若干類似之處。文化創(chuàng)造提供了無限的可能性,每一種可能性只要是能夠逐漸精微地表達人類的思維,就具有同等價值,這里沒有好壞高下之分。人為地將“屈折語”說成是最高級,將“孤立語”說成最低級,這要么是文化中心主義、種族偏見的自我欣賞和自我陶醉,要么就是民族虛無主義的自卑心理的表現(xiàn),而不是科學的分析。
文字領域的情況與語音領域的情況相似。
在文字的起源階段,用“象形”表達人類思想與語言中用“象聲”表達人類思想類似,同樣舍棄了許多東西,僅從客觀事物中抽出一些主要的特征寫畫下來。“米”是一棵果樹上結(jié)了許多果子的象形。但作為自然界的一種有機生命體,一棵樹是多么繁復的植物,結(jié)下的豐碩的果實也決不止三個。當我們用象形文字表達它的時候,失落了不計其數(shù)的果實了,而且用3個小圓圈代替了具有萬千特征的甜美的果實,又不知失落了多少屬性了。我們甚至不能說,我們所造的那個象形字就一定是抓住了果樹的形象的主要特征,其實它僅是從客觀物象中抽象出的極少一部分特征。這才是本色意義上的“抽象”。我們現(xiàn)在經(jīng)常掛在嘴上的所謂“抽象”,比如說小篆是漢字第一次規(guī)范化的字體,它字形固定,偏旁統(tǒng)一,這對于象形特點鮮明的甲骨文來說是一次抽象,而用點、橫、豎、撇、捺等筆畫轉(zhuǎn)寫篆書所發(fā)生的使?jié)h字變成純粹符號性質(zhì)的“隸變”又是更進一步的抽象,這些“抽象”,與文字最初形成階段的那次抽象相比,實在是小巫見大巫了。與語音的形成一樣,象形文字是各個民族根據(jù)不同的要求抽象出事物的極少特征寫畫下來,這使各種文字產(chǎn)生差距。中西文字目前巨大的差距是由各自不同的文化創(chuàng)造方法造成的。當美索不達米亞的字母被發(fā)現(xiàn)后,西方文字突然掉轉(zhuǎn)頭去走了一條拼音化的道路,而漢字則沒有走這條道路,依然按照原來的路徑發(fā)展著。于是,中西文字便相去遙遠了。“中國自殷商通用至今的表意方塊字,與發(fā)源于美索不達米亞,后來流行于世界大多數(shù)地區(qū)的拼音文字其淵源和特性都迥然相異,成為世界文化史上獨成一統(tǒng)的特例。”[③]
方塊漢字與拼音文字在結(jié)構(gòu)上的區(qū)別,我們認為也是“二維”與“三維”的區(qū)別。從漢語語音角度提出來的問題是與漢字的特點相吻合的。漢字的三維性使其具有立體性特點。但要證明漢字是三維的立體性結(jié)構(gòu),我們的面前有一道“定論”的銅墻鐵壁,一般認為,拼音文字記錄一個詞是用一串字母作線性的排列,在漢字往往用一個平面型方塊來表示,所以“漢字是平面型文字”[④]。誠然,漢字是寫在紙上的,不是雕塑在空間的,何以認為漢字是三維的因而具有立體性特點呢?這是因為漢字是用二維去展示、象征三維空間的,我們是就其所表達、所象征的意義上來說它是“三維”的。“立體派”的繪畫何以能稱“立體”呢?難道就不是畫在平面畫布上的嗎?
漢字主要起源于原始圖畫,而圖畫是用二維空間來表示三維空前的,那么,漢字就其起源階段的象形性而言,亦具有這樣的特征。漢字起源階段的這種象形的特性是漢字三維性發(fā)生學上的依據(jù),圖畫的形象性的特點是使人們可以直觀或感受到所畫事物“體”的質(zhì)感。例如,屬于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陜西華縣柳子鎮(zhèn)出土的陶器上。
即使是最逼真的工筆也不能將客觀事物的全部屬性和特征描繪出來,它在描繪中已經(jīng)遺漏了許多屬性和特征,因而,從某種意義上說,圖畫反映客觀事物也是“抽象”的。而漢字又是對象形圖畫的再一次“抽象”,這就使文字成為一種純粹的符號了。這種符號只要沒有變成音響形象的附屬物(如拼音文字那樣),這種三維立體性特點便沒有被打破,無論其抽象程度怎樣地越來越高。
從現(xiàn)實生活的客觀事物中抽象出來的以象形為基礎的文字,在其后來的發(fā)展變形過程中,并未改變其三維立體性特點,這是由于漢字后來無論怎樣變形,皆未徹底打破原有的符號體系去另辟新路。先看小篆。小篆是漢字第一次規(guī)范化的字體。比起甲骨文和金文來,小篆字體固定,并將原來沒有固定形式的各種偏旁統(tǒng)一起來,小篆的線條不再是去描畫客觀事物,而是變成了規(guī)則勻稱的帶弧形的整齊線條,就此而言,對漢字的立體性的沖擊是大的。但是,從根本上看,小篆并未改變漢字的結(jié)構(gòu)特點,而僅在原來的基礎上進一步抽象,只是線條略略變化,使文字同客觀事物的聯(lián)系更加隱蔽了一些。這樣的特征實在太多,無庸贅述。隸書的情況又怎樣呢?用點、橫、豎、撇、捺等筆畫轉(zhuǎn)寫篆書,這是被稱作“隸變”的漢文字史上的一場大變革,這場變革是古文字和今文字的分水嶺。從甲骨文到小篆,漢字線條的主要特點在于描摹客觀事物,因而它是畫出來的;而隸變后的五種基本筆畫則是寫出來的。由于隸變改變了筆畫的形態(tài),因而使?jié)h字形體發(fā)生了大的變化,變成純粹符號性質(zhì)的文字,基本擺脫了古漢字的圖形意味。后來,魏晉至隋唐出現(xiàn)的楷書,結(jié)構(gòu)與隸書基本相同,點、橫、豎、撇、捺等筆畫進一步發(fā)展,從此,漢字成為方塊字就定型了。但是,隸變以后的漢字并未改變漢字的三維立體性特點。我們還是以“為”字后來變化為例來說明。
這些形式亦分別積淀了大象的鼻子、軀體以及四條腿的內(nèi)容。由此看來,隸變中的漢字形體的改變僅是漢字結(jié)構(gòu)內(nèi)部進行自身調(diào)整時的一種較大的形態(tài)轉(zhuǎn)移,而不是漢字整體結(jié)構(gòu)的打破與重建,因而漢字立體性這一基本特點并未失落。
我們認為漢字在其發(fā)展的歷史長河中,其立體性特點一直保持著,但同時我們又認為隸變前后漢字立體性的特點又有著不盡相同的內(nèi)涵。適應于描摹客觀事物的各種形態(tài)、方向、長短、曲直的甲金文和小篆的線條,一變?yōu)檫m應于書寫的、長短大致統(tǒng)一、曲直有規(guī)則、形態(tài)方向一致的隸書、楷書和現(xiàn)代簡體的線條,這說明隸變使?jié)h字從圖畫意義上的立體性變成了幾何意義的立體性。隸變前的漢字通過用極簡約的線條描畫事物達到立體性,這種立體性因與圖畫類似,較易為人們認識,隸變以后的漢字實在有類于“立體派”的繪畫。它將對象世界引歸到立體幾何的方塊形體中去,呈現(xiàn)出一種多視點把立體平鋪到平面上的傾向。即“對一個物體作分解,同時從不同的方面,不只是從一個視點,提供了許多元素,把這些元素重新組合,相互疊置,相互滲入成為一個整體形象,這使得平面自身直接顯現(xiàn)立體感,卻又不是取消了平面,使它成為一個空間盛器,讓各種東西在它里面裝著”。[⑥]隸變后漢字不僅有“橫”“豎”兩種筆畫(這可以在垂直狀態(tài)下構(gòu)成平面),而且斜線(撇、捺)和點,斜線其實就是線條的水平放置狀態(tài),它與“橫”、“豎”垂直狀態(tài)所構(gòu)成的平面相交,便構(gòu)成立體圖形。“點”的意義亦如此,它其實在透視意義上是遠處的一條線或一個面;本身已造成了一種距離感和空間感,只要我們眼前出現(xiàn)了相交或平行直線構(gòu)成的平面,那么遠處的那個點就一定不可能與這個平面處在同一平面上,而只能是處在立體的空間中。漢字的三維立體性就這樣通過五種筆劃構(gòu)成了。這里,“關鍵是在于保持著具體的平面,而同時在象征的意味里,使它成為體積的空間意味的。”[⑦]
關于漢字的三維立體性,我們還可以從中國古代的書法理論中找到證明。衛(wèi)夫人《筆陣圖》對漢字的幾種筆劃有如下的說法:
這雖是一種比喻和象征,但是我們不難看出中國古代書家的潛意味深處是將漢字的筆畫當作某種客觀事物來看待的。這實際上是一種原始觀念的積淀,因為在原始人那里是沒有比喻可言的。進一步講,中國書法理論中所講的關于筆畫分布的結(jié)體理論更是漢字的立體性特點決定的。“中宮”和“重心”的理論,都是解決立體性字體結(jié)構(gòu)穩(wěn)定問題;“布白”理論則直接導源于文字的立體性:例如筆劃的“疏密得宜”是解決立體性眾多平面交叉的問題;“虛實相間”的說法是處理立體結(jié)構(gòu)中視覺看得見和看不見的關系問題;而所謂“爭讓得勢”則又是回答立體結(jié)構(gòu)中的主要平面與次要平面的表現(xiàn)關系等等。中國書法最忌平板,例如“馬”字下面的四點,楷書一般將第一、四兩點寫得較大,二、三兩點寫得較小,以示遠近關系。這些,皆可說明漢字的立體性特點。
我們論定漢字不同于拼音文字的三維立體性特點,這就為認識漢字的科學價值打下了基礎;而漢字的生命力正建立在這種科學價值的前提之上的。
漢字的立體性特點決定了漢字具有容量大、信息多、內(nèi)涵豐富的科學價值。我們?nèi)匀挥脭?shù)學的方法來說明。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一橫一豎和一條斜線(—|/),如果按拼音文字的線性排列,只有六種排列形式:—|/,—/|,|—/,|—/,/—|,/|—,但是,按立體性文字排列,其形式卻極多。橫豎構(gòu)成平面,而斜線當它放到立體性圖形中去的時候,位置可以相接、也可以相交,還可以相離。人們只需要從這極多的可能排列中選擇出目視區(qū)別較為明晰的排列用于造字就足夠表達人類各種各樣的概念。這從科學角度證明了漢字的方塊結(jié)構(gòu)是完全勝任表達人類的千差萬別的細微變化的概念。它也不見得就顯得繁復,因為它不需要用向外擴展的方式去表達,而只需在這個立體結(jié)構(gòu)框架的內(nèi)部就可以表達。如果說一個方塊漢字因筆畫多而顯得繁復,那么,一個英文詞用一大串字母排成一條線同樣也是繁復的。漢字的這個特點也是中國語言文字(尤其是文言)無形態(tài)變化,無時態(tài)變化,無冠詞的最根本性的決定原因。進而使中國語言文字比印歐語言“更易于打破邏輯和語法的束縛,從而也就更易于張大語詞的多義性、表達的隱喻性、意義的增生性,以及理解和闡釋的多重可能性。”[⑧]這正是在二十世紀語言學革命以后重新認識語言生命力的一把金鑰匙。一些有眼光的西方學者已經(jīng)認識到漢字和漢語的生命力,而另一些西方學者例如伊斯特林,認為漢字終究是一種有缺陷的文字,是文字發(fā)展低級階段上的文字,進而認為漢字是缺乏生命力的文字,這實在是一種對語言文字表達人類思維的特點缺乏全面認識所致。
注釋:
①伊斯特林:《文字的產(chǎn)生與發(fā)展》,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571頁。
②高明:《中國古文字學通論》,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49頁。
③馮天瑜、何曉明、周積明:《中華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4頁。
④胡裕樹:《現(xiàn)代漢語》,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88頁。
⑤皮亞杰:《結(jié)構(gòu)主義》,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第19頁。
⑥瓦爾特·赫斯編著:《歐洲現(xiàn)代畫派畫論選》,人民美術出版社,1980年版,第71頁。
一、關于黃帝文化
黃帝文化不僅是研討會的主要議題之一,也是探討精神家園建設的重要契機。研討會在黃帝文化方面主要討論了黃帝文化的特色、現(xiàn)代價值和精神內(nèi)涵等。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劉志琴研究員認為黃帝文化具有強烈的生命和生活意識,“中華民族對黃帝的尊崇,實際上尊崇的是生養(yǎng)、培育中華民族的生命之基,所以中華文明初始的象征不是神廟、金字塔那種固定的建筑實體,而是有生命的,鮮活的人中之杰――黃帝。從傳說時代就以現(xiàn)實生活而不是神物靈異作為中華文化的象征,這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特色”(《人文初祖的現(xiàn)代意義》)。山東經(jīng)濟學院王繼訓教授指出黃帝文化具有很強的文化象征、情感紐帶和精神感召作用,對中華民族、中華文明導向力的形成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在團結(jié)各族人民、振奮民族精神、推動文明建設等方面具有積極的作用(《黃帝與中華文明的導向力》)。
西北大學劉寶才教授認為,“黃帝文化的基本精神,即中華民族的偉大凝聚精神和創(chuàng)新精神,是黃帝時代歷史特征的總結(jié)”,“現(xiàn)有的黃帝文化的各種資料的性質(zhì)不完全相同,與黃帝時代的關系不完全相同,未必全都反映黃帝時代的歷史真實。作為觀念史的黃帝文化,它既與五千年前的黃帝時代聯(lián)系在一起,又與五千年來的中國文明史聯(lián)系在一起,在黃帝時代以來的五千年間得到不斷豐富發(fā)展”(《黃帝文化論綱》)。陜西師范大學趙世超教授通過對歷史典籍的考察辨析認為,“黃帝的傳說產(chǎn)生于北方,黃帝族的活動范圍沒有超出黃河流域”,在梳理黃帝形象歷史演變的基礎上,揭示了浙江縉云黃帝文化以道教文化為核心的本質(zhì),并強調(diào)拜祭人文初祖的活動不能走上背離人文主義精神的道路(《黃帝與黃帝文化的南遷》)。
二、關于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
研討會在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方面展開了深入研討,取得一系列成果。
關于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內(nèi)涵。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副會長王俊義教授認為“中華民族精神家園,乃是中華民族在歷史長河中形成的民族精神,通過物質(zhì)的與非物質(zhì)的載體和標志予以集中反映,呈現(xiàn)于民族大家庭之中,既有益于民族精神的凝聚與弘揚,又便于和世界各國家、各民族之間的思想文化交流”(《端正學風與民族精神家園建設》)。西北政法大學趙馥潔教授認為,“民族共有精神家園是民族共有的精神支柱、精神根基和精神寄托,是民族的‘安身立命之所,。具有自己的精神家園乃是一個民族具有主體性的深層內(nèi)涵和核心標志。民族精神家園是由宇宙意識、價值觀念、道德情懷和思維方式所構(gòu)成的精神系統(tǒng),其核心是價值觀念和價值理想”(《黃帝文化是構(gòu)建民族精神家園的寶貴資源》)。陜西師范大學周偉洲教授認為,“‘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并非只建設共有的‘精神’,而是包括了培育這種‘精神,的載體,‘家園’也就是實實在在的環(huán)境和氛圍”,從精神生活和物質(zhì)生活、社會(國家、家庭)環(huán)境和自然環(huán)境角度強調(diào)了精神文化所憑依的載體的重要價值;“‘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是包括中華民族56個民族在內(nèi)的‘共有’精神家園,也是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大家庭共有的精神財富。它不僅僅指從56個民族精神中抽象出來的都具有的精神財富,也應包括所有民族和地區(qū)多元文化中優(yōu)良的精神財富”(《中華文化與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建設》)。陜西師范大學楊恩成教授認為,“不能把‘民族精神’框范在一個狹窄的范疇內(nèi),忽視了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多民族性和多元性。這是我們談守護民族精神家園的出發(fā)點”,堅持和弘揚“以和為貴”的民族精神(《談民族精神家園的內(nèi)涵及其現(xiàn)代意義》)。陜西省政協(xié)原副主席陸棟先生認為,“精神家園是獲得身心自由、張揚生命意義的目標和歸宿;精神家園又是一種文化的存在,一種詩意的存在”,“精神家園其實是一個心靈轉(zhuǎn)化的過程,是一種開放和追求,一種安頓生命的體驗”(《文化?教育?師道――對民族精神家園建設要素的若干思考》)。清華大學程鋼副教授認為,“家園不是一個簡單的經(jīng)濟利益共同體,它同時又是一個充滿溫情與相互理解的精神家園”(《經(jīng)典閱讀與民族共同精神家園的建設》)。
關于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特征。周偉洲教授認為主要包括民族性、多元一體性、包容性、創(chuàng)新性及時代性(《中華文化與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建設》)。西北大學方光華教授認為天人合一、順乎人性、和而不同構(gòu)成了傳統(tǒng)核心價值觀念的理論框架,關于文化經(jīng)典的重新詮釋是中國傳統(tǒng)核心價值理論革新的主要方式,中國傳統(tǒng)核心價值觀念的傳播形式主要是教化,目的是塑造人的道德(《中國傳統(tǒng)核心價值理論的主要特點及建設經(jīng)驗》)。
關于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實踐途徑。首先是強調(diào)教育的價值。西北大學張豈之教授認為民族精神家園建設的基礎是現(xiàn)代公民文化科學素質(zhì)的全面提高,應該加強教育的普及和提升(《關于“弘揚中華文化、建設民族精神家園”的一點理解》)。教育部原副部長周遠清先生強調(diào)“在高等教育中,弘揚中華文化特別要加強人文文化與科學文化相和諧的建設,它是大學教育的歷史使命”,著重“培養(yǎng)學生的和諧文化思維、和諧文化觀念與和諧文化精神,用和諧文化豐富學生的精神世界,引導學生樹立和諧的思想觀念、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弘揚中華文化是我國大學的歷史使命》)。徐州建筑職業(yè)技術學院張俊相教授主張弘揚“大學之道”,繼承和發(fā)揚中華傳統(tǒng)的人文道德精神,建設高等學校的精神家園(《弘揚“大學之道”,建設高校精神家園》)。西北大學李浩教授認為大學文化、大學精神、大學校園建設等概念在我國理論界早于民族精神家園概念提出,它們在神圣性、包容性、開放性、儀式性與創(chuàng)新性等方面為民族精神家園建設積累了豐富的經(jīng)驗(《大學精神探索對民族精神家園建設的啟示》)。陸棟認為教育要貫穿中國文化的精神,“將中國文化的理想與人才培養(yǎng)的實際相結(jié)合,培養(yǎng)出有民族文化自覺和現(xiàn)代文化素養(yǎng)的人”(《文化‘教育?師道――對民族精神家園建設要素的若干思考》)。程鋼副教授認為“傳統(tǒng)經(jīng)典可以作為知識的核心與媒介,從而促進多元一體的成分之間達成文化的共識,最終推動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建設”(《經(jīng)典閱讀與民族共同精神家園的建設》)。浙江大學何俊教授、陸敏珍副教授認為現(xiàn)代社會的基本特征是理性化的,但經(jīng)驗性依然在發(fā)揮作用,區(qū) 域性的自足平衡系統(tǒng)仍然存在,它們對解決精神家園建設的問題具有深刻的影響(《網(wǎng)絡狀中國傳統(tǒng)社會及其現(xiàn)代轉(zhuǎn)型》)。
其次,突出文化認同與現(xiàn)代性反思的意義。周偉洲教授著重指出加強宣傳教育提高民族自覺的文化保護意識、正確處理各民族發(fā)展弘揚優(yōu)秀民族文化與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辯證關系等(《中華文化與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建設》)。北京師范大學瞿林東教授則認為要繼承和發(fā)揚歷史認同與文化認同相統(tǒng)一的優(yōu)良傳統(tǒng)(《中國史學:中華民族一個共有的精神家園》)等。湖南大學肖永明教授認為建設中華民族精神家園應當立足于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繼承、重視兼容會通、體現(xiàn)時代要求(《關于建設中華民族精神家園的幾點思考》)。中國藝術研究院任大援教授從文化自覺角度闡述了精神家園建設的具體思路,從古代儒家注重道德自覺的倫理本位出發(fā),分析建設共有精神家園的有用資源,重點論述了儒家實現(xiàn)道德自覺的道德實踐方法,即學以明倫的倫理實踐、效法天地自然的情感實踐、養(yǎng)氣立志的君子人格實踐的現(xiàn)代價值(《精神家園建設與文化自覺》)。北京語言大學李慶本教授從傳播學角度分析了中國文化與傳播對象國之間的關系與解決途徑(《中華文化傳播對象國的文化政策研究報告》)。陜西省社會科學院佘樹聲研究員、西安佛教研究中心韓金科研究員通過對殷商、西周、東周出現(xiàn)的倫理認知和倫理觀的比較,認為當時氏族家族血緣紐帶關系倫理認知發(fā)展到了頂峰,并且促使非氏族家族血緣關系倫理認知和倫理體系產(chǎn)生,構(gòu)成了中國歷史文化發(fā)展百家爭鳴自由學術環(huán)境的觀念基礎,形成了中國古代道德倫理與政治倫理的歷史框架(《春秋戰(zhàn)國時期民族精神的建構(gòu)》)。
關于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意義。河北經(jīng)貿(mào)大學武占江教授從人的有限性和無限性,重新反思理性與信仰、義與利、理與欲的關系,認為“重新構(gòu)建精神家園是挽回人的尊嚴、維持人的幸福的必要手段”(《精神家園與人的尊嚴》)。暨南大學范立舟教授認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認同研究能夠強化民族凝聚力,促進全球華人在價值規(guī)范和思想品性方面的共同觀念,培育天下一家、和而不同的廣闊胸襟,為建構(gòu)現(xiàn)代中國的新型文化體系提供思想保障(《天下歸心:中國傳統(tǒng)文化之認同性問題研究》)。學者們認為經(jīng)濟全球化的浪潮帶來了民族文化的全球性傳播,加速了民族文化的交往與碰撞,使民族文化的認同問題變得更加尖銳和突出。沒有對民族精神的自覺,民族文化將可能被全球化的浪潮所淹沒。
三、關于黃帝文化與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關系
黃帝文化與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之間的聯(lián)結(jié)點是研討會的一個重點和難點,研討會在若干問題認識上有所突破。
強調(diào)文明的傳承和革新。張豈之教授認為,黃帝文化是中華文明的起源,是構(gòu)建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寶貴資源,體現(xiàn)了時代性與民族性的有機統(tǒng)一,黃帝文化與繼承發(fā)揚民族精神的關系是“源”與“流”,“實質(zhì)是‘繼往’與‘開來’。推陳出新、繼往開來是學術生命力的表現(xiàn),如果沒有創(chuàng)新,就會使文化失去活力;從另一方面看,如果否定繼承,又可能迷失本原。‘繼往’同‘開來’相互聯(lián)系,‘推陳’與‘出新’是辯證的統(tǒng)一”(《關于“弘揚中華文化、建設民族精神家園”的一點理解》)。
突出信仰的意義和價值。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建筑西北設計院總建筑師張錦秋教授認為“黃帝陵是中華兒女共同景仰的圣地。在漫長的歷史歲月之中,黃帝陵已成為海內(nèi)外華人公認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園的標志之一。繼續(xù)做好,不斷完善黃帝陵的保護與建設工作對弘揚中華文化、激勵愛國熱情、增加民族凝聚力、建設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園,具有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完善黃帝陵的保護與建設,建設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園》)。中央民族大學牟鐘鑒教授重估黃帝信仰的價值,認為黃帝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時期的共祖,是中華民族的締造者和中華早期文明的集大成者,在他身上凝聚著整個民族的智慧和創(chuàng)造,“在中華民族由弱變強的今天,在中國人由文化自卑走向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覺的時候,深入認識黃帝信仰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正確解讀黃帝文化的內(nèi)涵和精神,并發(fā)揮黃帝文化在團結(jié)各族人民、振奮民族精神、推動文明建設中的積極作用,就成為一項需要全社會共同關心和參與的重要工作。”他認為“黃帝信仰是將祖源認同與文化認同合為一體,不單純是血統(tǒng)的探源,同時也是文化的尋根。黃帝信仰整合了民族的統(tǒng)緒,使中華民族之中各個民族有一個共同的心理歸屬,起到了鞏固中華共同體的作用”,“突顯了中華文化的精神,開啟了文化民族主義的先河”(《文化學的視野:黃帝信仰與中華民族》)。
彰顯黃帝文化的現(xiàn)代意義。趙馥潔教授認為,“經(jīng)歷五千年之久的‘黃帝文化’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由歷史記載、神話傳說、文物遺跡和祭祀活動構(gòu)成的黃帝文化中積淀和凝結(jié)著豐厚淵深的精神價值內(nèi)涵。自古以來,對黃帝的歷史探索和歷史紀念總是與弘揚這些優(yōu)秀精神價值融合為一體的。黃帝文化中蘊涵的精神價值,是我們今天構(gòu)建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寶貴資源”,包括贊美文明創(chuàng)造的人文價值、崇尚“惟仁是行”的道德價值、追求統(tǒng)一和諧的社會價值理想、奮力振興中華的民族精神價值(《黃帝文化是構(gòu)建民族精神家園的寶貴資源》)。陜西歷史博物館楊東晨研究員從天下為公精神角度闡發(fā)和梳理了關于黃帝與中華民族精神的關系研究,認為“黃帝精神是原始社會發(fā)展到社會即將轉(zhuǎn)型、物質(zhì)達到史前豐富階段的產(chǎn)物,也是上承‘三皇’下啟‘三代’之重要時代的精神結(jié)晶。其以土地為根發(fā)展經(jīng)濟、以民生為本創(chuàng)造發(fā)明、以和合為綱建立古國的精神,可以綜合概括為‘天下為公’的偉大精神,亦可泛稱為‘黃帝精神”’(《弘揚黃帝為公精神,建設民族和諧家園――兼論黃帝與中華民族精神形成的內(nèi)在關系》)。
揭示黃帝文化構(gòu)建精神家園的歷史過程。寶雞文理學院高強教授認為,至遲在春秋戰(zhàn)國時期,人們已普遍認為黃帝是人們的共同遠祖,這種祖先認同的趨勢為戰(zhàn)國時期的黃帝崇拜現(xiàn)象、秦漢時期的大一統(tǒng)局面、為華夏族的正式形成奠定了觀念基礎和心理基礎,“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形成與發(fā)展的過程中,黃帝起著構(gòu)建共同心理的重要作用”(《黃帝與中華民族》)。臺灣明道大學李增教授認為黃老之道,“以《老子》之道為先,《黃帝四經(jīng)》在后,老子之道著重在玄虛,《四經(jīng)》之道在落實”,它們共同奠定了中華民族文化的精神基礎(《黃老之道比較與對中華民族精神之貢獻》)。南開大學張榮明教授認為秦漢是中國中古政治信仰的創(chuàng)立期,通過比較分析,揭示了政治信仰從實到虛以及與政治理性的密切聯(lián)系(《秦漢政治信仰建設及啟示》)。
四、關于中華文化
研討會對中華文化的豐富性、深刻性、現(xiàn)代性也作了充分揭示,特別勾勒了中華文化 在建設民族精神家園方面的積極意義。
關于中華文化的精神內(nèi)涵。張豈之教授認為“中華民族復興是經(jīng)濟、政治和文化的全面復興,缺一不可。經(jīng)濟上的貧困,人民生活如果沒有持續(xù)的提高,沒有普遍的富裕,就無力支撐民族的發(fā)展。而單純經(jīng)濟上的提升,沒有政治和文化與之協(xié)調(diào)發(fā)展,也無力塑造一個偉大的民族”,主張將中華文化與民族的興旺發(fā)達聯(lián)系起來考察,突出中華文化的民族性與時代性的統(tǒng)一,這是新時期弘揚中華文化的立足點和出發(fā)點;弘揚中華文化、建設民族精神家園,主軸是精神文明,包括中華文化的特有精神內(nèi)涵和當代人對待民族精神家園的價值取向(《關于“弘揚中華文化、建設民族精神家園”的一點理解》)。北京大學樓宇烈教授認為儒家學說是一種“成人”之學,教育人成為一個真正有道德的人,以“修身”為中心的“成人”學說具有鮮明的實踐特性,也是儒學的生命力與現(xiàn)代性所在(《儒家學說的實踐性格》);他在學術發(fā)言中深入分析了古代祭天禮所體現(xiàn)的豐富文化內(nèi)涵,包括報本觀念、效法和遵循天道的意識、以天德要求自己的以德配天思想,對中國哲學史上的天道與人道關系問題做了新的闡發(fā)。西安交通大學鐘明善教授認為中華民族傳統(tǒng)文化思想有兩個主要觀念,即陰陽對立統(tǒng)一觀念、易和變觀念,并且體現(xiàn)在書法藝術的創(chuàng)作理論與實踐中(《中華民族傳統(tǒng)文化思想與書法藝術》)。華中師范大學劉固盛教授認為“道家的生命關懷精神,是道家思想的精髓部分,在現(xiàn)代社會尤具特殊意義”,主要體現(xiàn)為以平等、主體、至上的原則珍視、安頓、關懷生命,既重視現(xiàn)實的形體生命,又主張回歸自然,保持精神生命的自由,以獲得生命的圓滿與超越(《論道家的生命關懷精神》)。
關于中華文化的特點和價值。周偉洲教授認為,中華文化具有多元一體、變異性和穩(wěn)定性的基本屬性,是“由眾多民族融合形成的漢族與其他古今眾多少數(shù)民族長期文化交融的結(jié)果”,構(gòu)建和弘揚現(xiàn)代中華文化必須高度重視和堅持保護中華文化(包括構(gòu)成其基礎的各個民族傳統(tǒng)多元文化),合理地、可持續(xù)開發(fā)和利用中華文化中各民族多元文化的遺產(chǎn),推動思想和理論的發(fā)展與創(chuàng)新(《中華文化與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建設》)。
關于中華文化與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相互關系問題。趙馥潔教授認為“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重要途徑是弘揚中華文化,特別是繼承和弘揚中華文化中所蘊涵的優(yōu)秀精神價值”(《黃帝文化是構(gòu)建民族精神家園的寶貴資源》)。周偉洲教授認為“中華文化應是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前提、根據(jù)和基礎;而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是中華文化,特別是其中優(yōu)良的精神文化的升華和重新構(gòu)建”,中華文化發(fā)展、創(chuàng)新的過程即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發(fā)展、創(chuàng)新的過程(《中華文化與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建設》)。陜西師范大學朱士光教授從歷史地理學角度論述中國傳統(tǒng)文化在建設生態(tài)文明中的重要價值,認為在黃帝時代就已有“天人和諧論”的萌芽,強調(diào)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發(fā)掘了中國古代文化典籍蘊藏的豐富的保護自然、謀求可持續(xù)發(fā)展的思想,結(jié)合歷史地理的變遷討論了環(huán)境生態(tài)破壞等問題,強調(diào)生態(tài)文明是世界上一切文明的共同基礎,確立儉樸節(jié)約的生態(tài)倫理觀與生活習俗是建設生態(tài)文明的基本途徑。建設生態(tài)文明也是建設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重要保障和內(nèi)容(《從天人和諧論到建設生態(tài)文明的偉大實踐》)。
關于學風建設與中華民族精神家園的關系。王俊義教授指出,端正學術研究領域中的風氣,是展開學術研究與發(fā)揚民族精神的重要保障,強調(diào)精神家園建設必須依托學術研究,注重學術研究的嚴肅性和科學性(《端正學風與民族精神家園建設》)。
關鍵詞:音樂藝術;中國傳統(tǒng)音樂;結(jié)構(gòu)特點;哲學基礎;文化特征
中圖分類號:J60-02文獻標識碼:A
一、中國傳統(tǒng)音樂的結(jié)構(gòu)特點
(一)以“腔”為基礎的中國傳統(tǒng)音樂結(jié)構(gòu)層次
在中國傳統(tǒng)音樂結(jié)構(gòu)中,“腔”是一個帶有全局性,具有音樂形態(tài)學、音樂結(jié)構(gòu)學和音樂美學諸多方面意義的概念。
在音樂形態(tài)學方面,沈洽指出:“所謂腔,指的是音的過程中有意運用的,與特定的音樂表現(xiàn)意圖相聯(lián)系的音成分(音高、力度、音色)的某種變化”①。單音,猶如語言學中的“字”一樣,是結(jié)構(gòu)音樂活體中的一種最小的有機元素。中國音樂體系的傳統(tǒng)音樂中,單音作為一個音過程來理解時,可能出現(xiàn)的音高變化通常是一種“遞變量”,形成“曲線狀”的音過程。并且這種貫穿著音高、力度、音色變化的音過程的單音,成為中國傳統(tǒng)音樂的主流樂音。而在歐洲傳統(tǒng)音樂中,單音是一種“直線式”的音過程,音與音之間構(gòu)成“躍進”的關系;雖然在歐洲的某些傳統(tǒng)音樂樂種中也存在著“歌腔”,但是,這種歌腔指的是一個起主導作用的音樂主題,是一句有特色的旋律,即使其中個別樂音有音高、力度、音色的變化,卻并沒有成為主流,因為其樂音基本生成因素之一的語言屬于重音語言,而不同于中國音樂體系大多數(shù)民族使用的是漢藏語系的聲調(diào)語言,這種“腔”音在歐洲傳統(tǒng)音樂中不具備普遍意義,沒有上升到主導地位。
在音樂結(jié)構(gòu)學意義方面,中國傳統(tǒng)音樂的“腔”,從字義上看,具有框架的意義。《辭海》中,對“腔”字的第一種解釋是:“動物體內(nèi)的空隙或室。如體腔、胸腔、腹腔、圍心腔、圍腮腔、血腔、外套腔、生殖腔等。” ②《現(xiàn)代漢語詞典》中,“腔”也是這種意義:“動物身體內(nèi)部空的部分:口腔、鼻腔、胸腔、腹腔、滿腔熱血、爐腔兒。” ③指的都是動物體內(nèi)的空的部分,并且具有框架的意義。《辭海》和《現(xiàn)代漢語詞典》中,對“腔”的另外一種解釋,就更明確地指出:“腔”是“曲調(diào);唱腔。如:昆腔;字正腔圓。”④“樂曲的調(diào)子:高腔、花腔、昆腔、唱腔兒、唱走了腔兒。”⑤這里的“腔”,主要指的是一種曲調(diào)框架,曲調(diào)樣式。這種框架、樣式,既具有一種約定俗成的規(guī)式性,甚至提煉概括為“程式”,成為行內(nèi)人必須遵循的某種藝術的法式、規(guī)范,形成程式性;又具有可以根據(jù)唱詞內(nèi)容、感情的變化和演奏者情緒、靈感作即興發(fā)揮的變易性。所謂“樂之筐格在曲,而色澤在唱。” ⑥這種“筐格”就是“腔”,在音樂結(jié)構(gòu)層次中就包括:腔音、腔音列、腔節(jié)、腔韻、腔句、腔段、腔調(diào)、腔套、腔系的約定俗成的規(guī)式性,或程式性;“色澤”就是演唱演奏時的即興變易性,包括各結(jié)構(gòu)層次內(nèi)部的可變性,在一定筐格內(nèi)的變易和創(chuàng)新。
在音樂美學意蘊方面,“腔”已經(jīng)成為中國傳統(tǒng)音樂的一種基本美學追求。聲樂中的“依字行腔,字正腔圓”,“腔依調(diào)行”,“以腔傳情”等;器樂曲中的“定板正腔”,“死曲活腔”,“腔不韻則不美”等。都表現(xiàn)出對“腔”的重視,對“神韻”的追求。在此,神韻在很大程度上是與“腔”聯(lián)系在一起的,神韻是腔的目標和內(nèi)涵,腔是神韻的外顯和載體。試想,如果在現(xiàn)實音樂生活中,將民歌、戲曲、曲藝的歌唱和器樂旋律的演奏,都按鋼琴上“直線式”“躍進式”的固定音高來呈現(xiàn)的話,那將會是一種什么樣的效果呢?人們肯定會認為,這是一種“洋腔洋調(diào)”,失卻了中國傳統(tǒng)音樂的神髓和韻味。就像是品慣了鐵觀音的人,突然喝一杯白開水那樣,感到索然無味。這就從另一個側(cè)面證明,“腔”在中國傳統(tǒng)音樂及其結(jié)構(gòu)美學中的基礎地位。
正是因為上述三個方面的原因,所以,筆者在對中國傳統(tǒng)音樂的各結(jié)構(gòu)層次,都冠以“腔”為定語,分別稱之為:腔音,腔音列,腔節(jié)與腔韻,腔句,腔段,腔調(diào),腔套,腔系。
1.腔音
在中國傳統(tǒng)音樂結(jié)構(gòu)層次中,“腔音”(帶腔的音)與歐洲傳統(tǒng)音樂的單音一樣,都是結(jié)構(gòu)音樂活體中的一種最小的有機元素。它們的主要區(qū)別在于:歐洲傳統(tǒng)音樂的單音作為一種過程來理解時,是一種音高感的持續(xù),是“直線式”的音過程,音與音之間構(gòu)成“躍進”關系;而“腔音”(“帶腔的音”)可能出現(xiàn)的音高變化則通常是一種“遞變量”,是“曲線狀”的音過程,同時還有“與特定的音樂表現(xiàn)意圖相聯(lián)系的音成分(音高、力度、音色)的某種變化”。 ⑦
2.腔音列
腔音列,指的是由兩個或兩個以上樂音所構(gòu)成的音樂結(jié)構(gòu)的基本單位。如果說,“帶腔的音”所包含的音成分變化是“音自身的變化”的話,那么,如同詞是語言結(jié)構(gòu)中可以獨立應用的基本單位一樣,在這里,腔音列指的就是“不同音的組合”的最小單位。它最少包括兩個音,一般由三個音或四個音組成。樂音之間的音程關系是腔音列的基礎,無半音五聲性的腔音列并置是中國五聲性調(diào)式的基礎。腔音列的節(jié)奏組合并不強調(diào)輕重拍的變化,而只強調(diào)緊松、松緊的組合關系。
3.腔節(jié)、腔韻
腔節(jié)與歐洲傳統(tǒng)曲式中的樂節(jié)相類似,是介于腔音列與腔句之間的結(jié)構(gòu)單位,由數(shù)個腔音列組成,有一個停頓,但尚未像腔句那樣是“完整的一句話”,相當于語言中的頓號或逗號。腔節(jié)與樂節(jié)的主要不同在于其中往往存在著一個性質(zhì)特殊的部分:腔韻。
腔韻,是樂曲中最具特性,因而也是最為典型的音調(diào)。從結(jié)構(gòu)上看,它與按一定語法規(guī)則組合成的詞組相似。腔韻在曲調(diào)的反復循環(huán)中,在一定的結(jié)構(gòu)地位中,保持不變或基本不變。從規(guī)模看,與歐洲傳統(tǒng)音樂中的樂節(jié)所不同的是樂節(jié)只限于某一樂句中的某一組成部分,而腔韻卻在許多樂句、或結(jié)構(gòu)的其它部分反復出現(xiàn),并且在較為固定的位置反復出現(xiàn),成為一種貫穿性的結(jié)構(gòu)單位,作為某一腔調(diào)或腔系的重要標識,而區(qū)別于其他腔調(diào)或腔系。
4.腔句
在中國傳統(tǒng)音樂中,腔句與語言學中的“句”有類似之處。“句”,包含有詞、語法、句式、音調(diào)(平仄)等內(nèi)容。腔句在曲調(diào)中所包括的板式、句幅和句式等內(nèi)容,也與歐洲音樂的樂句有一定的對應關系,而且兩者關系甚為密切。只是,中國傳統(tǒng)音樂的各種不同曲牌、板式,其約定俗成的規(guī)則更為嚴格,有一定的起落音、開唱和結(jié)束的板眼位置、唱詞句式的字數(shù)和平仄要求、旋律音調(diào)的骨干音、節(jié)奏的大致模式等規(guī)制。而歐洲傳統(tǒng)音樂中的樂句,除了方整性句式和非方整性句式中的前者要求結(jié)構(gòu)上的對稱,以及古典音樂各樂句的功能性規(guī)律之外,比較少程式性的規(guī)制。
5.腔段
在中國傳統(tǒng)音樂中,腔段與歐洲傳統(tǒng)音樂的樂段相對應。但是,腔段在所包含的腔句數(shù)量、各腔句的句幅、骨干音、起落音、起落板眼位置等方面,都有較為嚴格的規(guī)定。
6.腔調(diào)
腔調(diào),指的是按照一定格式而組成的曲調(diào)框架。歷來有所謂“樂出既成,曲依調(diào)行”的說法,此“調(diào)”就是腔調(diào)。其主要特點在于曲調(diào)框架的規(guī)式性和具體運用時的靈活性。曲調(diào)框架的規(guī)式性指的是在各特定腔調(diào)中,對于腔韻的運用,腔句的數(shù)量,各腔句的字數(shù)、平仄、起落音、骨干音、起落音的板眼位置、句式長短等都有一定的程式規(guī)范。靈活性指的是在具體運用時可以根據(jù)唱詞內(nèi)容、感情表達的需要,在遵循一定規(guī)范的框架內(nèi),作即興性的行腔、潤腔處理,使之變得更為豐富動人。而在歐洲音樂尤其是歐洲專業(yè)創(chuàng)作音樂中,并沒有曲調(diào)框架的規(guī)式性,而是以“專曲專用”的創(chuàng)作方式,每一樂曲創(chuàng)作不同的曲調(diào)框架,一旦形成新曲調(diào),其具體運用時的靈活性是十分有限的。
7.腔套
腔套是多種腔調(diào)依一定章法聯(lián)結(jié)而成的套曲。在中國傳統(tǒng)音樂中,它可能是一個腔調(diào)的反復或變化反復,也可能由幾個不同的腔調(diào)聯(lián)結(jié)接而成。然而,無論是單腔調(diào)疊體腔套,或者是多腔調(diào)聯(lián)體腔套,它們的腔調(diào)聯(lián)結(jié)也都有一定的規(guī)式。如:在單腔調(diào)疊體腔套中,有“散、慢、中、快、散”的板式連接規(guī)律,不同聲腔(如:西皮、二黃)不能直接連用等;在多腔調(diào)聯(lián)體腔套中,按各腔調(diào)的感情氣質(zhì)、宮調(diào)歸屬、旋律特性等,分為多種腔調(diào)類別,并形成了較為嚴格的、約定俗成的連接規(guī)范。在歐洲音樂中,尤其是專業(yè)音樂創(chuàng)作中,提倡專曲專用、多種專曲聯(lián)為專套等。
8.腔系
多種有內(nèi)在聯(lián)系的腔調(diào)及其變體,形成具有不同地域風格、不同體裁特征、不同表情功能特點的腔調(diào)系統(tǒng),即構(gòu)成腔系。中國傳統(tǒng)音樂的這一結(jié)構(gòu)層次,當與傳統(tǒng)創(chuàng)作方式的“一曲多變運用”有關,即往往在原有熟悉的曲調(diào)之中填入新的唱詞,或者運用一首耳熟能詳?shù)那{(diào)進行各種各樣的變奏,而形成新的唱腔、民歌或樂曲。久而久之,一首腔調(diào)由不同地區(qū)的藝術家在不同體裁類別中,運用來表現(xiàn)不同的唱詞或不同的感情,由此而衍化成多種變體,這些變體集合在一起,于是就形成了腔調(diào)體系,簡稱腔系。腔系這一結(jié)構(gòu)層次在歐洲音樂尤其是文藝復興之后的歐洲專業(yè)創(chuàng)作音樂中是不存在的。從本質(zhì)上看,當我們對腔調(diào)與樂曲,腔套與組曲、套曲進行類比之后,就可以得出這樣的結(jié)論:腔系,是中國傳統(tǒng)音樂所特有的一種結(jié)構(gòu)層次,它形成了自身的一套獨特的變化發(fā)展規(guī)律。
(二)各音樂結(jié)構(gòu)層次的規(guī)式性和可變性
在中國傳統(tǒng)音樂的各個結(jié)構(gòu)層次中,幾乎都有一定的規(guī)式性和可變性。
所謂規(guī)式性,就是在長期的藝術實踐中,各民族、各地域、各樂種、各流派,都形成了各個結(jié)構(gòu)層次內(nèi)部的約定俗成的規(guī)定和范式,只有遵循這些規(guī)范才能得到本民族、本地域、本樂種、本流派的承認。如“帶腔的音”的音高、力度、音色變化幅度、特色;腔音列的民族、地域、樂種、流派的典型性;腔節(jié)、腔韻、腔句、腔段、腔調(diào)、腔套、腔系在結(jié)構(gòu)、特性、旋律、音調(diào)、起落音、節(jié)奏、板式、板位等方面的規(guī)式性等。符合規(guī)式者,得以承認;不符合規(guī)式者,得不到認可。
所謂可變性,指的是“樂之筐格在曲,而色澤在唱” ⑧。即:在遵循以上規(guī)式的基礎上,可以根據(jù)唱詞所表現(xiàn)的內(nèi)容、感情的需要,按演唱演奏者的情緒、感受、靈感作即興演唱、演奏,進行創(chuàng)造性變易。也就是說,可以進行“一曲多變運用”。即:在運用一個基本曲調(diào)框架來表達多種樂思的過程中,對其腔音、腔音列、腔節(jié)、腔韻、句式、腔句等方面所進行的變化。
在變易原因方面,有:內(nèi)容、感情性變易,民族性變易,地域性變易,樂種性變易,流派性變易,情緒、生理性變易等。
在變易原則方面,有重復與變化重復原則、對仗原則、對比原則、展衍原則、起平落原則、起承轉(zhuǎn)合原則。
在變易手法方面,有重復法(含嚴格重復,換頭、換尾、合頭、合尾、疊字、垛句等變化重復);變奏法(含:板式、節(jié)奏變奏法、旋律變奏法、遞增遞減的數(shù)列節(jié)奏變奏法、移宮換調(diào)變奏法);展衍法(含:引申式展衍、承遞式展衍);集聯(lián)拆穿法(即:集曲、聯(lián)套、拆句交錯、穿插連體);變腔法(含:音區(qū)變換法、伴奏樂器定弦變換法、調(diào)式變換法)等。
雖然花樣翻新,五彩繽紛,但是在基本腔調(diào)及其各種變體之間,總能尋探出諸多聯(lián)系,是在一定規(guī)式性基礎上的變易。所謂“帶著腳鐐的舞蹈”,一旦將這腳鐐拋棄,完全打破既成框架,不顧這既定的規(guī)式性,反倒是跳不起來,唱不舒暢、奏不順手了。這就是“一曲”與“多變運用”的辯證關系。
(三)中國傳統(tǒng)音樂結(jié)構(gòu)思維方式、創(chuàng)作方法之“漸變”特點
1、結(jié)構(gòu)內(nèi)部的漸變
結(jié)構(gòu)內(nèi)部的漸變,指的是在結(jié)構(gòu)內(nèi)部各個結(jié)構(gòu)層次變化的量的逐漸變化和過程的圓融與柔和。
在結(jié)構(gòu)原則方面,中國傳統(tǒng)音樂與歐洲音樂的差異在于:前者強調(diào)統(tǒng)一,后者強調(diào)對比。中國傳統(tǒng)音樂偏重于采用在統(tǒng)一基礎上呈現(xiàn)對比的原則,常以漸變的方式來展開樂思,講求自然、順暢的變化。歐洲音樂偏重于采用在對比的基礎上完成統(tǒng)一的原則,常用突變的方式來展開樂思,追求鮮明、強烈的對比。
在一個樂音的構(gòu)成以及樂音與樂音之間的連接方式上,中國傳統(tǒng)音樂中,“帶腔的音”的音過程常有音高、音色、音強的變化,音與音之間常用“腔”把兩個點連接起來,呈現(xiàn)出曲線狀、弧線狀,體現(xiàn)了漸變原則。歐洲音樂中,樂音本身構(gòu)造的穩(wěn)定性,音與音之間由點到點的躍進式、直線性狀態(tài),體現(xiàn)了突變原則。
在兩個以上樂音的組合方面,中國傳統(tǒng)音樂的腔音列以大二度、小三度連接為基礎,以三音列的并置為特點,強調(diào)其連貫性和色彩性。歐洲音樂則常由幾個樂音組成一個動機,以動機在不同音區(qū)、不同調(diào)性上重復、模進、變形,來展開樂思,是動機在橫向、縱向上的跳躍變化。
在旋律展開手法方面,中國傳統(tǒng)音樂較多采用以某一腔調(diào)為基礎,用加花、添眼、換頭、展衍等手法來展開樂思,基本上是一個腔調(diào)在橫向上逐漸變化。歐洲音樂則強調(diào)段落之間的對比,常用由不同音樂素材構(gòu)成的段落對比來推動音樂發(fā)展。在各個腔調(diào)或腔段內(nèi)部,中國傳統(tǒng)音樂常用魚咬尾、連環(huán)扣、句句雙、展衍等線性漸進、蜿蜒游動、自由綿延式的手法來展開樂思。歐洲音樂(尤其是器樂作品)常以不同的音樂主題和調(diào)性的對比來推動段落內(nèi)部的音樂發(fā)展。
以單腔調(diào)疊體和多腔調(diào)聯(lián)體為基本形式的中國傳統(tǒng)音樂的腔套,其結(jié)構(gòu)布局的特點是強調(diào)統(tǒng)一,有貫穿性的腔韻、節(jié)奏型,在統(tǒng)一的基礎上逐步變化,展開樂思。結(jié)構(gòu)類型以更為講究聯(lián)系、統(tǒng)一的“起、承、轉(zhuǎn)、合”為主,即使是類似于歐洲音樂三部曲式那樣的“起平落”類型,也與歐洲音樂ABA式不同,或者為ABC式,或者為ABA1式, B與A之間的對比往往較為模糊,具有較多的內(nèi)在聯(lián)系。以三部曲式(ABA)為代表的歐洲音樂曲式則強調(diào)對比,在對比基礎上完成統(tǒng)一;其變奏曲也包含展開式的變奏,在整體布局上隱伏著三部曲式的結(jié)構(gòu)框架。
在中國傳統(tǒng)音樂的大、中、小腔套中,其速度的快慢組合、板式的散整連接雖然多種多樣,既有以散板為開始,接以慢板、中板、快板,最后以散板結(jié)束的,也有散、整、慢、快交錯的,但是較為普遍的是“散―慢―中―快―散”布局,呈現(xiàn)出漸變的大趨勢。歐洲音樂中的三部曲式或組曲,常用的是“快―慢―快”或“慢―快―慢”的速度布局,強調(diào)速度的對比和突變。
在調(diào)式結(jié)構(gòu)和調(diào)轉(zhuǎn)換方面,中國傳統(tǒng)音樂以無半音五聲音階為基礎,音級之間以大二度、小三度連接為主,即使有近似于小二度的連接,也屬于中二度,而沒有導音傾向性,各種調(diào)式也不像歐洲大小調(diào)體系那樣地強調(diào)各音級的功能性;移宮換調(diào)時,經(jīng)常采用“變宮為角”(往上方五度調(diào)轉(zhuǎn)換)、“清角為宮”(往下方五度調(diào)轉(zhuǎn)換)的手法,過渡自然順暢。歐洲音樂的大小調(diào)體系強調(diào)調(diào)式的導音傾向性和功能性,亦即強調(diào)調(diào)式各音級之間調(diào)性之間的力度關系、對比關系,轉(zhuǎn)調(diào)時調(diào)性對比鮮明。
2、結(jié)構(gòu)的歷時性漸變
結(jié)構(gòu)的歷時性漸變,指的是中國傳統(tǒng)音樂中,同一腔調(diào)雖然有民族性變易、地域性變易、樂種性變易、審美性(流派性)變易、感情內(nèi)容性變易、情緒生理性變易等,但是,在比較長的時間段內(nèi),仍然保持著量的漸變,并沒有達到質(zhì)的突變。雖然歷經(jīng)二三百年或者更長時間的變易,西皮、二黃還是京劇的主要聲腔,【春調(diào)】腔系依然是各地民歌的主要腔系,各宮調(diào)曲牌及其聯(lián)套仍舊是昆曲的主要組成部分。
昆曲,產(chǎn)生于元末明初江蘇昆山一帶,系由南曲與當?shù)孛耖g音樂相結(jié)合衍變而成。明嘉靖(1522―1566)、隆慶(1567―1572)年間,魏良輔、梁辰魚、過云適、張野塘等人對之進行改革,創(chuàng)“水磨腔”以來,雖經(jīng)400多年,衍化出南昆、北昆、湘昆、永昆等多種風格的昆曲流派,在京劇、川劇、湘劇、婺劇、祁劇、贛劇、桂劇、柳子戲等劇種中,根據(jù)各劇種風格特點進行變化改革而保留著它的部分唱腔和器樂曲牌,但是這些流派、劇種中各相對應的相同曲牌,仍具有較為統(tǒng)一的曲調(diào)框架而形成同一的昆曲各宮調(diào)腔系,體現(xiàn)了在漸變中所保留的共性。
【春調(diào)】腔系,來源于江南一帶的唱春活動,后來傳遍東西南北,形成民族性春調(diào)腔系、地域性春調(diào)腔系、體裁性春調(diào)腔系、樂種性春調(diào)腔系、流派性春調(diào)腔系、腔套性春調(diào)腔系等。幾百年來,在全國各地雖然五彩繽紛,花樣翻新,但是,仍能尋出它們在腔音列、腔韻、主要腔句落音、句式、腔句等方面的聯(lián)系。這也說明了貫穿在各個層次的變易仍屬漸變性質(zhì),萬變不離其宗。
西皮、二黃這兩個聲腔系統(tǒng)伴隨著京劇的歷史而形成和發(fā)展。自清代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徽班進京,二百余年以來,歷經(jīng)眾多優(yōu)秀表演藝術家的藝術創(chuàng)造,出現(xiàn)了多種多樣的板式,性別、氣質(zhì)、性格各異的行當唱腔,各具音樂風格特點的流派唱腔,劇情內(nèi)容、思想感情細致生動的劇目唱段,雖然潤腔、行腔不斷豐富,旋律音調(diào)、唱腔結(jié)構(gòu)幅度多有變化,加上京二胡等伴奏樂器,但是西皮、二黃各自作為一個聲腔系統(tǒng),它們都保留著共同的特點:各板式的基本調(diào)式相同;各板式的旋律起伏線和骨干音基本相同或大同小異;各板式每句唱腔的基本幅度大致相同;同腔各板式每句唱詞第一字和最末一字的起落腔位置相同,西皮為眼起板落、二黃為板起板落;各板式除導板、回龍為單句體之外,各板式均為由上下句構(gòu)成一個基本腔段。也就是說,皮黃聲腔的行當唱腔、流派唱腔、劇目唱腔的“變”都是在“漸變”,都是在“量變”,并沒有突破其基本框格的“突變”、“質(zhì)變”。
對于中國傳統(tǒng)音樂結(jié)構(gòu)的這種漸變特點,借用梅蘭芳、程硯秋的話是十分恰切的說明。梅蘭芳說:“移步不換形”。 ⑨這雖然是對他自己畢生藝術經(jīng)驗的總結(jié),但同時也是對包括梅蘭芳所創(chuàng)作的梅派唱腔在內(nèi)的中國傳統(tǒng)音樂結(jié)構(gòu)發(fā)展變化規(guī)律的概括,也即黃翔鵬所指出的:“傳統(tǒng)音樂根據(jù)自己口傳心授的規(guī)律,不以樂譜寫定的形式而凝固,即不排除即興性、流動發(fā)展的可能,以難于察覺的方式緩慢變化著,是它的活力所在,這就是‘移步不換形’的真諦。” ⑩程硯秋說:“守成法,要不拘于成法;脫離成法,又要不背乎成法。”B11提倡以“成法”為依據(jù),進行變化發(fā)展,但是這種變化是在傳統(tǒng)“成法”基礎上的漸變。只有這樣才能符合中國傳統(tǒng)音樂的發(fā)展規(guī)律,才能得到群眾的首肯。正如程硯秋自己說的:“以我個人的經(jīng)驗來說,我感到京劇的腔調(diào)本來很簡單,但改腔時要在原來的基礎上慢慢地給它變化、發(fā)展,這樣觀眾容易接受。……創(chuàng)腔時總要慢慢的變化、發(fā)展,先改變一點,觀眾覺得新鮮但不陌生,再改一點,又與以前不同;慢慢地發(fā)揮,以后就可以什么都引進來,又新奇、又熟悉、又好學、又好聽。這就是觀眾的心理。”B12
在繼承中發(fā)展,發(fā)展必須以繼承為基礎,循序漸進,蜿蜒流動,順暢自然,這就是中國傳統(tǒng)音樂結(jié)構(gòu)變化的規(guī)律。
二、哲學基礎――“道生一”、“三生萬物”與“中庸之道”
(一)“道生一”
“道生一”,就是“道”為本,“一”為基。
“道”,作為中國哲學的一個基本范疇,王蒙指出:道,指的是“一個包羅萬物萬象眾生眾滅萬世萬有的同一的本質(zhì)、規(guī)律、道理、法則、過程、道路、同一性。這個本質(zhì)就是道。為了與一般的各種具體的道相區(qū)別,我們有時稱之為大道。”B13據(jù)王蒙的闡釋,老子所謂的“道”有三大特征。“第一,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第二,……它追求的是概括與統(tǒng)一。其一是存在與本質(zhì)的統(tǒng)一。……其二是大道的本體、本容與本源的統(tǒng)一。……其三,它統(tǒng)一了道、德、天、自然等概念,一而同之,強調(diào)了它們的同一性與唯一性。……其四,它忽略了、超越了物與心、客觀與主觀、有神論與無神論的差別,也統(tǒng)一了人們對于世界與人類的基本認知。第三,老子的這些認識,既是先驗的也是概括的與經(jīng)驗的。他自以為可以超越先驗與經(jīng)驗的分野,超越(宗教)信仰、哲學、審美以及與邏輯論證的差別。它凸顯了中國式的整體的一攬子的思維方法。”B14
作為一對范疇,中國古代多有關于“道”與“器”的論述。
先秦,《周易•系辭上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B15認為“道”是形而上的抽象的規(guī)律、原則、道理等;“器”是形而下的具體的天地、動植物、器械等。
唐代,孔穎達在《周易正義》說:“道是無體之名,形是有質(zhì)之稱。凡有從無而生,形由道而立。是先道而后形,是道在形之上,形在道之下,故自形外已上者謂之道也,自形內(nèi)而下者謂之器也。形雖處道器兩畔之際,形在器不在道也。”B16提出了先“道”后“器”的觀點,“道”是無體的名稱,“形”是有質(zhì)的名稱,先有“道”而后有“形”,這就是“無中生有”的命題。
據(jù)張立文研究,“‘道’與‘器’真正作為一對哲學范疇而受到重視則在宋明時期,理學各派按照他們對‘理’與‘氣’、‘心’與‘物’的關系的理解,對‘道’與‘器’的關系作出了不同的規(guī)定。程、朱學派以‘理’為其哲學邏輯結(jié)構(gòu)的最高范疇。故以形而上之‘道’為‘理’。”B17
程頤以“理”與“氣”喻“道”與“氣”,認為,陰陽是“氣”,是形而下之“器”;“道”則是形而上的“理”。他說“離了陰陽更無道,所以陰陽者是道也。陰陽,氣也。氣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形而上者則是密氣。”B18
朱熹用“道”與“器”的關系來說明“理”與“氣”的關系,認為:“太極便與陰陽相對,此是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B19“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器也。”B20并且用“道”與“器”、“形而上”與“形而下”喻“理”與“氣”。他說:“陰陽,氣也,形而下者也;所以一陰一陽者,理也,形而上者也。道即理之謂也。”B21主張“道”是所以陰陽者,而“道”非陰陽。他說:“至于《大傳》既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矣,而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豈真以陰陽為形而上者哉!正所以見一陰一陽雖屬形器,然其所以一陰一陽者,是乃道體之所為也。”B22主張“道在器中”、“道器為一”,“道”必依“器”而有頓放處。他說:“愚謂道器之名雖異,然其實一物也。故曰吾道一以貫之。……愚謂道器一也,示人以器,則道在其中。”B23朱熹的學生陳淳又提出“道亦器,器亦道”,注意二者之間的聯(lián)系,以明確形而上、形而下的區(qū)別。陳淳說:“其實道不離乎器,道只是器之理。人事有形狀處都謂之器,人事中之理便是道。道無形狀可見,所以明道曰:‘道亦器也,器亦道也’。須著如此說,方截得上下分明。”B24
王夫之則主張將“道”與“器”形而上、下說和“道”與“器”一體論結(jié)合起來,既論證其分二相對,又論證合一不離,從而把“道器”論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他說:“天下惟器而已矣。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謂之道之器也。無其道,則無其器,人類能言之。……無其器,則無其道,人鮮能言之,而固其誠然者也B25。”
在中國傳統(tǒng)音樂結(jié)構(gòu)中,“道生一”的“道”,應當是客觀現(xiàn)實對于人的主觀的刺激,引起人的情感反應。所謂“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B26。”這里的“人心之感于物”就是“道”之本。由此“生一”,而產(chǎn)生音樂結(jié)構(gòu)的基本框架,于是有了“一”之基。《樂記》中說:“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動,故形于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B27。”這段文字實際上將“道”為本、“道生一”、“一”為基的過程和內(nèi)涵作了明確的闡述。即:音的產(chǎn)生,緣起于人有能夠產(chǎn)生思想感情的“心”。人的思想感情的激動,是外界事物給予影響的結(jié)果,這就是“道”為本。受外界事物的影響使感情激動起來,以“聲”的形式表現(xiàn)出來,這是“道生一”,由“道”產(chǎn)生一種“聲”。“聲”在互相應和之中,顯示出變化,長短、徐疾、高低、繁簡、輕重、明暗變化的“聲”,按照一定的規(guī)律組織在一起,叫做“音”。把“音”按照一定的結(jié)構(gòu)關系演奏起來,加上舞蹈,就叫做“樂”(此“樂”為音樂與舞蹈相結(jié)合的綜合體,是為某一體裁形式、某一腔調(diào)的基本形態(tài),“一為基”)。
(二)“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體現(xiàn)了“一與多”、“有限與無限”的哲學命題。
首先,是“一”為基。
老子曰:“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候王得一以為天下貞B(tài)28。”按照王蒙的闡釋,“大道的特點是它的唯一性、統(tǒng)一性、完整性、一元化,所以大道即一。自古以來,得到而這個偉大的一的主體當中,如果天得到了這個一,天就清晰明朗了。地得到了這個一,地久平安穩(wěn)定了。眾神得到了在這個一,眾神就靈驗了。山谷、谷地得到了這個一,就充盈豐滿了。萬物得到這個一,就有了自身的存在與形成了。侯王得到了這個一,就可以成為天下的標桿了”。B29
筆者認為,對于中國傳統(tǒng)音樂結(jié)構(gòu)來說,可以加一句:“樂得一以成。”即:樂得到了這個一,樂就可以“成人”、“成形”、為基。“成人”者,孔子曰:“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B30。”詩可以使人振奮,禮使人在社會上能站得住,音樂使學業(yè)得以完成,使人完美高尚。“成形”者,樂得到了這個一,樂的腔調(diào)的基本形態(tài)能夠得以形成。在中國傳統(tǒng)音樂的“樂”中,“一”是基,“一”是源,“一”是歸。源一,釋一,歸一。
“一”是源。中國傳統(tǒng)音樂結(jié)構(gòu)的諸多要素都源于“一”。
“一”拍子,源于唱詞的板式,均以一板為基礎,由×,生出××,×××,×× ×××,×× ××|×××|。
“一”基礎腔音列,由大二度、小三度連接而成的腔音列,由sol-la-高音do,變化出la-高音do-re,還有do-re-mi。
“一”原型基因,童忠良創(chuàng)用“集合原型樂理求解法”B31。求出徵類色彩三音列為中國傳統(tǒng)音樂五聲調(diào)式的原型基因,其始列音為基礎音列的第一音sol,它與徵類色彩三音列sol、la、高音do各樂音所構(gòu)成的音程依序為:“0,2,5”個半音;由原型基因派生出逆反型基因和衰減基因;羽類色彩三音列為逆反型基因,其始列音是羽類色彩三音列的音程冠音高音re,它與羽類色彩三音列l(wèi)a、高音do、re各樂音所構(gòu)成的音程依序為:“5,2,0”個半音;以兩個大二度的連接為材料的“宮、商、角”,含兩個大二度與一個大三度的衰減基因,是一個“倒影相等集合”,無論是以“宮”為始列音,或者是以“角”為始列音,它們的音級都是“0,2,4”。B32
“一”原型腔韻,基本腔韻為中音區(qū)的中腔韻,由此派生出高音腔韻、低音腔韻、長腔韻、短腔韻和截韻。
“一”種基本句式,“一”種曲調(diào)框架的基本形態(tài)。
“一”種基本音色――人聲音色。貴人聲,重自然,其余音色都是對人聲的模仿或追尋。
以上許多變體,都是對“一”的詮釋,為“釋一”。最終又是“歸一”,回歸于一體,回歸于“一”。各種腔套,各種腔系,各種流派,各樂種,各地域支脈,各民族風格,萬變不離其宗,全部都歸于中華民族多元一體這個“一”。
第二,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根據(jù)張立文的研究B33,“殷商之際的《周易》中,已含有沖突觀念的萌芽。到了春秋戰(zhàn)國時代,提出了‘物生有兩’和‘一體而兩分’的思想。”B34
史墨在《左傳》中說:“物生有兩,有二,有五,有陪貳。……故《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B35這里的“物”是事物或統(tǒng)一物,“兩”即相反、相對,由兩而引申為貳,有下逆上的意思,高岸與深谷、深谷與山陵是相互轉(zhuǎn)化。
老子提出“道生一,一生二”,是以“道”代替史墨的“物”,“一生二”則與“物生有兩”有相似之處。從“二”出發(fā),老子對沖突互相轉(zhuǎn)化也有所體認,提出了如下的諸多轉(zhuǎn)化:“曲則全,枉則正,洼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B36
“一分為二”的思想,在《莊子》、《周易》、《呂氏春秋》中先后以“日取其半”、“太極生兩儀”、“一體而兩分”來表達。《莊子•天下》曰:“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B37《周易•系辭上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B38“分而為二以象兩,卦一以象三。”B39《呂氏春秋》曰:“父母之于子也,子之于父母也,一體而兩分,同氣而異息。”B40
漢唐時期的先哲則較多注意合二為一。董仲舒說:“天之常道,相反之物也,不得兩起,故謂之一。一而不二者,天之行也。”B41“是故古之人物而書文,心止于一中者,謂之忠;持二中者,謂之患。”B42
王充改造了董仲舒“凡物必有合”的思想,認為“合”就是沖突的結(jié)合、融合,從而產(chǎn)生新的事物。王充說:“夫天地合氣,人偶自生也。猶夫婦合氣,子則自生也B43。”“然天地、夫婦也,合為一體。”B44這里的“天地合氣”、“夫婦合一”就是相對待兩方的融合,從而和合為新事物。B45今人王蒙則說:“改革開放以來,哲學家龐樸提倡一分為三,既對立的兩方面斗爭的結(jié)果應該是第三個方面,新的方面,用王蒙的話來說是新一代的方面出現(xiàn)。……承認第三種情勢、第三個方面出現(xiàn)的可能性與必要性這是一個巨大的飛躍。……我尊重一,并警惕一的僵局僵硬。我懂得二,并迎接二的挑戰(zhàn),琢磨二的協(xié)調(diào)的可能性。我歡迎三,并注意三漸漸成了一以后還有一、二、三的分化與萬物雜多共生,情勢會愈來愈復雜化B46。”這就是“三生萬物”。
在中國傳統(tǒng)音樂的各種結(jié)構(gòu)層次和整體結(jié)構(gòu)中,都存在以上這三種“一生二”的情況,即:“一生二”更傾向于“一分為二”,“一生二”更傾向于“合二為一”,由“一生二”到“二生三”、“三生萬物”。但同時,也都存在對待方的相互作用和沖突,即“沒有對待沖突,就沒有統(tǒng)一物;沒有統(tǒng)一物,則對待的作用也就止息了B47”。
如前所述,在中國傳統(tǒng)音樂的五聲調(diào)式基因中,由原型基因這個“一”,通過逆反變化、衰減,“一分為二”生發(fā)出逆反型基因、衰減基因;但是,無論逆反型基因,或是衰減基因都與原型基因保持統(tǒng)一的因素。逆反基因以羽類色彩三音列的冠音為始列音,計算出它與各樂音所構(gòu)成的音程之半音數(shù),正好是原型基因的反向順序,逆反型為“5,2,0”個半音,原型為“0,2,5”個半音。衰減基因的三音列框架由原型基因的純四度(sol-la-高音do)框架變?yōu)榇笕?sol-la-si=do-re-mi,fa-sol-la=do-re-mi)框架,造成音程半音數(shù)的減少,由原型的“0,2,5”個半音衰減為“0,2,4”個半音,其中仍可尋出它們之間的聯(lián)系。
在腔音列方面,如果說中國五聲調(diào)式的原型腔音列是徵類色彩窄腔音列的話,那么,由此“一分為二”生發(fā)出羽類色彩窄腔音列、近腔音列;再“二生三”、“三生萬物”,生發(fā)出徵類色彩寬腔音列、羽類色彩寬腔音列、大腔音列、小腔音列;進而出現(xiàn)減腔音列、增腔音列。并且通過各種不同的混融、交錯、擴展、衰減,產(chǎn)生出眾多的民族性典型腔音列、地域性典型腔音列、樂種性腔音列、流派性腔音列,甚至于曲目性腔音列,豐富多樣,異彩紛呈。然而,它們都以大二度和小三度為基本生成因素,這就成了聯(lián)系中國音樂體系各種腔音列的紐帶。
在腔系中,由一個【春調(diào)】產(chǎn)生【孟姜女調(diào)】、【手扶欄桿】,再生發(fā)出【梳妝臺】、【鳳陽歌】、【四空仔】、【揚調(diào)】,由此進而產(chǎn)生【穿字梳妝臺】、【西皮梳妝臺】、【半妝臺】、【金派梳妝臺】,【四平調(diào)】、【慢四平】、【四平】、【快四平】、【反四平】、【高調(diào)反四平】,【七字正調(diào)】、【七字高腔】、【七字低腔】、【七字哭腔】、【七字反】、【七字中管】,【揚調(diào)慢板】、【揚調(diào)中板】、【揚調(diào)連扳】、【揚調(diào)垛板】、【二流】、【散板】、【苦稟】、【苦稟中板】、【連板】、【垛板】、【散板】等。這一系列的變化過程,是不斷“一分為二”的過程,體現(xiàn)了“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的規(guī)律,所謂“萬物聚合起來便是‘一’,分衍開來即是世界萬物。因此,‘本一氣也,生則為陽,消則為陰,故二者一而已矣。……故有一則有二,有二則有四’”B48。
在中國傳統(tǒng)音樂的橫向性“漸變”和歷時性“漸變”,又體現(xiàn)了在“一生二”過程中對于“一分為二”的互相對待沖突、相互滲透融合關系的重視。朱熹贊成“萬物莫不有對”,采納“一物兩體”,提出陰陽相對待而又同處在一個統(tǒng)一體中,認為:“天下道理,只是一個包兩個”。B49“凡一事,便有兩端”。B50“天下萬物,未嘗無對,有陰便有陽,有仁便有義,……有動便有靜”。B51方以智則提出了“合二而一”的命題,認為事物都有對待的“兩端”,對待兩端又交合、融合、“二而一”,他說:“曰有,曰無,兩端是也。虛實也,幽明也,陰陽也,形氣也,道器也,晝夜也,幽明也,生死也,盡天地古今皆二也。兩間無不交,則無不二而一者”。B52“交也者,合二而一也”。B53
中國傳統(tǒng)音樂結(jié)構(gòu)內(nèi)部的橫向漸變,無論是樂音自身或樂音與樂音的連接,都有音高、音色、音強的變化,使之變得圓融,高低兩端交合自然。
由典型性腔音列構(gòu)成的腔韻及其在各相對固定結(jié)構(gòu)位置的反復出現(xiàn),使各相對待的腔句、腔段猶如對待的“兩端”那樣交合、融合,“二而一”。
腔句之間常用“句句雙”、“連環(huán)扣”、“魚咬尾”等旋律手法來展開樂思;腔套內(nèi)部常用一個腔調(diào)為基礎,以加花、減字、添眼、換頭、合尾、展衍等手法來進行變化發(fā)展;使各結(jié)構(gòu)個體(腔段、腔套)內(nèi)部的各個對待的“兩端”(腔節(jié)與腔節(jié)之間、腔句與腔句之間、腔段與腔段之間、腔調(diào)及其變體之間)又交合、又融合、“二而一”。
在大、中、小腔套的各部分板式、速度“散―慢―中―快―散”及其交叉的連接,“以變宮為角”“以清角為宮”的宮調(diào)轉(zhuǎn)換,以定弦變換法和“借字”、“壓上”相結(jié)合的腔調(diào)變體和宮調(diào)轉(zhuǎn)換,都體現(xiàn)了前后、上下的交合、融合,前中有后,后中有前,前后交融,渾然一體。
中國傳統(tǒng)音樂結(jié)構(gòu)的歷時性漸變,無論是民族性典型腔音列、地域性典型腔音列,或者是樂種性典型腔音列、流派性典型腔音列,最終都脫離不了中國音樂體系無半音五聲音階的大二度、小三度組合、連接,而沒有半音連接,尤其沒有導音傾向性,體現(xiàn)了中國音樂體系各民族之間的交合、融合、“二而一”。
腔調(diào)的基本形態(tài)及其各種變體之間,雖有多種由近到遠的關系不同的層次性,并形成層次性腔系,如:以民族性典型腔音列、腔韻、起落音、句式、腔句為特征的民族性腔系;以地域性典型腔音列、腔韻、起落音、句式、腔句為特征的地域性腔系;以樂種性典型腔音列、腔韻、起落音、句式、腔句為特征的樂種性腔系;以流派性典型腔音列、腔韻、起落音、句式、腔句為特征的流派性腔系等。各層次之間,各層次內(nèi)部都是不斷的“一分為二”,不斷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但是,它們之間的每對相鄰的兩端,無論在腔音列、腔韻、起落音,或者是句式、腔句等方面,都具有諸多聯(lián)系,體現(xiàn)了相對待兩端的交合、融合、“二而一”。
(三)“中庸之道”
中國傳統(tǒng)音樂結(jié)構(gòu)的漸變特點,還與儒家的“中庸之道”哲學觀相關聯(lián),即:“中”為規(guī),“執(zhí)兩用中”,以“中”為追求,以“中”為規(guī)范。
據(jù)張國慶研究,《尚書•盤庚》中篇,“盤庚在遷都前訓導臣民要‘各設中于乃心’。這個‘中’字,顧頡剛先生譯為‘中正’,王世舜同志譯為‘正道’(《尚書•譯注》),顯然是一種值得肯定的美德,一種正確的德行。……《尚書》里‘中’的基本含義,可以在‘正確’(準確、得當)上統(tǒng)一起來”。B54孔子在《論語•雍也第六》中說:“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鮮民久矣。”B55“這里的‘中’即是前述正確之意,它也就是《論語•堯曰》里‘允執(zhí)其中’的‘中’,楊伯峻先生釋之為‘最合理而至不移’。而‘庸’即‘用’,所謂‘庸,用也’,其完整的表述是‘執(zhí)兩用中’,意即掌握住事物對立兩端并在兩端間選擇、運用正確之點。”B56張國慶還從“義”、“時中”、“權(quán)”幾個范疇論述了“執(zhí)兩用中”的思想原則、方法論原則。認為,“義”是“宜”,追求“中”的具體標準是禮、仁、善、賢、信、智、直……等,各有其不同的適應面。“時中”,是要人們根據(jù)時代、環(huán)境和各種關系的變化發(fā)展去研究和把握彼時彼地的“中”,強調(diào)“中因時變,因時用中”。“權(quán)”,是權(quán)衡稱量、通權(quán)達變的意思,既有近于“義”和“時中”的含義,又是對一切事物是否合于“中”的具體衡量判斷,正如孟子說的:“子莫執(zhí)中,執(zhí)中無權(quán),猶執(zhí)一也。所惡執(zhí)一者,為其賤道也,舉一而廢百也B57。”
中庸之道對情感表達方式的要求是“樂而不,哀而不傷”B58。也就是快樂而不至于毫無節(jié)制,悲哀而不致傷害身心。不走極端,安于常態(tài)。對音樂藝術的審美標準也是如此。《尚書•舜典》載:“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B59《左傳•襄公二十九》載:“請(吳公子季札)觀于周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為之歌《邶》、《》、《衛(wèi)》,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wèi)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wèi)風》乎?’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為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其周公之東乎?’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為之歌《魏》,曰:‘美哉,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后,誰能若是?’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逼,遠而不攜;遷而不,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jié)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B60這里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勤而不怨、憂而不困、思而不懼、樂而不、大而婉、險而易行、思而不貳、怨而不言、曲而有直體、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逼,遠而不攜;遷而不,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jié)有度,守有序,都是基于“中庸之道”對音樂美的品鑒標準體現(xiàn)“執(zhí)兩用中”,以中為正,不偏不倚的中庸精神。
《禮記•典禮上》提出:“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B61《樂記》說:“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B62《禮記•中庸》中說:“喜怒哀樂之未發(fā)謂之中,發(fā)而皆中節(jié)謂之和。”B63都認為音樂之美不可超過限度,音樂形態(tài)以中正平和為宜,情感表達以中節(jié)適度為限。所謂“樂中平則民和而不流”。B64以中平之樂,培養(yǎng)謙和自守的道德人格。
漢代,劉向《說苑•修文》記載了孔子批評子路的故事,其主要原因也是由于子路未能領悟中庸的基本精神。孔子在批評子路的同時,指出:“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為中節(jié)。……故君子執(zhí)中以為本,務生以為基。故其音溫和而居中,以象生育之氣”。B65強調(diào)重視“中聲”、“中節(jié)”,“執(zhí)中以為本,務生以為基”,以溫和居中的音樂來“象生育之氣”。達到天地各安其位,萬物生長發(fā)育,萬事欣欣向榮,人世間充滿蓬勃生氣的境界。
在中庸之道的原則指導下,中國傳統(tǒng)音樂腔調(diào)在禮的制約下達到“執(zhí)兩用中”的規(guī)范,“不偏不倚”、“無過無不及”。在抒情時,強調(diào)節(jié)制,“發(fā)乎情,止乎禮儀”,“樂而不,哀而不傷”,“喜怒愛樂之未發(fā)謂之中,發(fā)而皆中節(jié)謂之和”,“情見而意立,樂終而德尊”。無論是文人音樂、宮廷音樂,或者是宗教音樂、民間音樂,都比較注意分寸感,講究恰到好處,強調(diào)“含蓄、蘊藉”。荀子在《樂論》中所論及的音樂表現(xiàn)手段和音樂形式規(guī)律,是具有一定典型意義的。他說:“樂則必發(fā)于聲音”,“使其曲直、繁省、廉肉、節(jié)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并且指出:“故樂者,審一以定和者也,比物以飾節(jié)者也,合奏以成文也。”B66此中的“審一以定和者”,指的是音樂之聲必須“中”而不“”,審察、選擇一個中聲作為基礎,確定宮音、主音,用以產(chǎn)生其它各音;進而以這一中聲為基礎來組織眾音,使樂思和諧展開。
由于以“中庸之道”為哲學基礎的中國傳統(tǒng)音樂結(jié)構(gòu),遵循著“執(zhí)兩用中”的規(guī)范,“不偏不倚”、“無過無不及”,所以,在其樂思展開過程中,無論是樂音個體、樂音與樂音之間的連接,腔音列的運用,或是旋律發(fā)展手法,板式、節(jié)奏、速度轉(zhuǎn)換,都講求“允執(zhí)其中”,連貫舒暢,過渡自然,圓融和合。就像是打太極拳那樣始終保持著圓形弧線,剛?cè)嵯酀?方圓適度。又像是我國的書法藝術一般,行云流水,骨力追風,在橫向的線的粗細、濃淡、曲直、剛?cè)岬臐u變中,表現(xiàn)出種種意趣、意境。
以“中”為規(guī)的中國傳統(tǒng)音樂,在處理各個結(jié)構(gòu)層次的規(guī)式性和可變性的關系中,循序漸進,在遵循規(guī)式中變易,在變易中繼承規(guī)式。旋律直而不倨,曲而不屈;節(jié)奏寬而栗、大而婉;五聲和,節(jié)有度,守有序;不追求華而不實、流而不中的外在的繁音促節(jié),而在變化有度、平和中正的奏唱中抒情、寫意,傳承變易。
總之,中國傳統(tǒng)音樂結(jié)構(gòu)以“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和“中庸之道”為哲學基礎,體現(xiàn)了“道”為本、“一”為基、“萬”為形、“中”為規(guī)的特點。(責任編輯:陳娟娟)
① 沈洽《音腔論》,《中央音樂學院學報》,1982年第4期,第14頁。
② 辭海編輯委員會編《辭海》1979年縮印本,上海辭書出版社,1980年版,第1518頁。
③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編《現(xiàn)代漢語詞典》,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1016頁。
④ 同②。
⑤ 同③。
⑥ 王驥德《曲律•論腔調(diào)第十》,葉朗《中國歷代美學文庫》“明代卷”(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4頁。
⑦ 同①。
⑧ 同⑥。
⑨ 張頌甲《移步不換形――梅蘭芳談舊劇改革》,《進步日報》,1949年11月3日。
⑩ 黃翔鵬《論中國傳統(tǒng)音樂的保存與發(fā)展》,《中國音樂學》,1987年第4期。
B11程硯秋《創(chuàng)腔經(jīng)驗隨談》,《音樂建設文集》中冊,音樂出版社,1959年版,第975頁。
B12同B11,第973頁。
B13王蒙《老子的幫助》,華夏出版社,2009年版,第10頁。
B14同B13,第11-12頁。
B15《周易•系辭上傳》,黃壽祺、張善文《周易譯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563頁。
B16《系辭上傳》第七,《周易正義》卷七,《十三經(jīng)注疏》本。
B17張立文《中國哲學邏輯結(jié)構(gòu)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94頁。
B18《河南程氏遺書》卷十五,《二程集》,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162頁。
B19《朱子類語》卷九十五。
B20《太極圖書說解》,《周子全書》卷一,萬有文庫本。
B21《通書•誠上注》,《周子全書》卷七,萬有文庫本。
B22《答陸子靜》,《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四部叢刊初編本。
B23《朱子類語》卷七十四。
B24陳淳《北溪字義》卷下,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39頁。
B25王夫之《系辭外傳》第十二章,《周易外傳》卷五,中華書局,1962年,第170頁。
B26《樂記•樂本篇》,中央音樂學院中國音樂研究所,1961年版,第19頁。
B27同B26。
B28老子《道德經(jīng)•下篇•四十二章》,《諸子集成》第三卷《老子道德經(jīng)》,上海書店影印出版,1986年版,第114、115頁。
B29同B13,第159頁。
B30同B28,第一卷《論語正義》,第160頁。
B31童忠良《集合原型的樂理求解》,《中國音樂學》,1989年第2期。
B32童忠良《五聲調(diào)式基因論》,《對稱樂學論集》,上海音樂學院出版社,2009年版,第195-201頁。
B33張立文《中國哲學邏輯結(jié)構(gòu)論》“一與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229―240頁。
B34同B33,第229頁。
B35同B33,第229頁。
B36同B28,第558頁。
B37同B28,《莊子•天下》,第580頁。
B38同B16,第556頁。
B39同B16,第548頁。
B40同B28第六卷《呂氏春秋》,《呂氏春秋•卷第九•季秋紀第九•精通》,第93頁。
B41董仲舒《春秋繁露•天道無二》,洪修平《儒佛道哲學名著選編》,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12頁。
B42同B41。
B43王充《論衡•物勢第十四》,《論衡校釋》卷三。
B44王充《論衡•說日第三十二》,《論衡校釋》卷十一。
B45同B17,第231頁。
B46同B13,第179頁。
B47同B17,第234頁。
B48同B17,第233頁。
B49《朱子語類》卷七十九。
B50《朱子語類》卷十三。
B51《朱子語類》卷九十五。
B52方以智《東西均》,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17頁。
B53同B52,第24頁。
B54張國慶《中國古代美學要題新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3頁。
B55同B28第一卷《論語正義》,第132頁。
B56同B54,第4頁。
B57《孟子•盡心上》,同B28,第一卷《孟子正義》,第541、542頁。
B58《論語•八佾》。
B59葉朗《中國歷代美學文庫》“先秦卷”(上),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99頁。
B60同B59,第270、271頁。
B61同B59,《禮記•典禮上》,第176頁。
B62同B59,《樂記•樂本篇》,“秦漢卷”,第222頁。
B63同B59,《禮記•中庸》,第221頁。
B64同B59,《荀子•樂論》,第290頁。
B65《中國文化精華全集•藝術卷》,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92年版,第114頁。
B66同B59,“先秦卷”(下卷),第290頁。
The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Philosophical Bas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Music
WANG Yao-hua
(School of Music,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