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fā)布時(shí)間:2022-07-16 11:21:28
開(kāi)篇:寫作不僅是一種記錄,更是一種創(chuàng)造,它讓我們能夠捕捉那些稍縱即逝的靈感,將它們永久地定格在紙上。下面是小編精心整理的1篇民事法律行為本質(zhì)思考,希望這些內(nèi)容能成為您創(chuàng)作過(guò)程中的良師益友,陪伴您不斷探索和進(jìn)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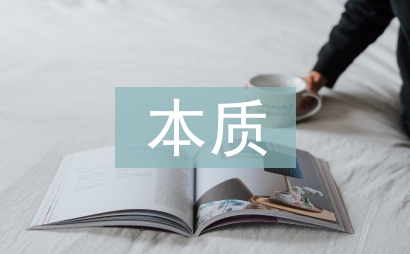
為在理論上徹底否定《民法通則》所采取的民事法律行為本質(zhì)合法說(shuō)觀點(diǎn),我們?cè)鴮?duì)該種觀點(diǎn)的歷史源流作過(guò)一些考察。通過(guò)考察發(fā)現(xiàn),該種觀點(diǎn)并非出于傳統(tǒng)民法理論(注:參見(jiàn)拙文:《論法律行為的合法與本質(zhì)》,《法律科學(xué)》1998年第5期。),相反,倒是發(fā)源于前蘇聯(lián)的民法理論。因?yàn)椋ㄟ^(guò)該觀點(diǎn)在前蘇聯(lián)民法理論中的萌生與傳播的事實(shí)可知,這種觀點(diǎn)雖然僅有觀點(diǎn)展示,而無(wú)確切形成依據(jù),但是,由于有 “意志法”理論的支持以及計(jì)劃經(jīng)濟(jì)體制推行的實(shí)際需要,使該觀點(diǎn)得到維持并且有相當(dāng)大范圍之?dāng)U散。20世紀(jì)50年代,伴隨著中國(guó)向蘇聯(lián)全面學(xué)習(xí)的風(fēng)潮興起,又使該觀點(diǎn)傳至我國(guó),并因此而成為《民法通則》確立民事法律行為概念的理論依據(jù)。鑒于此,本文的重點(diǎn)便在于說(shuō)明法律行為本質(zhì)合法說(shuō)觀點(diǎn)實(shí)系前蘇聯(lián)“意志法”理論及其計(jì)劃經(jīng)濟(jì)體制的產(chǎn)物,目的仍然是通過(guò)追本溯源而達(dá)到撥亂反正之效果。
一
事實(shí)表明,出自于前蘇聯(lián)民法學(xué)界個(gè)別人之手的法律行為本質(zhì)合法說(shuō)觀點(diǎn),由于“意志法”理論的出現(xiàn),使該種觀點(diǎn)身價(jià)倍增,并很快就擁有了自己的市場(chǎng)。這便表明,該種觀點(diǎn)首先就是“意志法”理論的產(chǎn)物。
第一,建國(guó)之初的蘇聯(lián),原本是持法律虛無(wú)主義治國(guó)觀念的,但由于斯大林的明確表態(tài),不僅使其所持的法律虛無(wú)主義治國(guó)觀念一掃而光,而且,還使“意志法”理論一躍而成為其意識(shí)形態(tài)的主旋律。
十月革命之后的蘇聯(lián),一開(kāi)始所形成的治國(guó)觀念是法律虛無(wú)主義的。因?yàn)楫?dāng)時(shí)的人們普遍認(rèn)為,既然社會(huì)主義是從資本主義向共產(chǎn)主義的過(guò)渡時(shí)期,那么,這一時(shí)期自然也就成為國(guó)家與法律的逐漸消亡時(shí)期。緣于此,在20世紀(jì)20年代,圍繞著過(guò)渡時(shí)期的法律性質(zhì)問(wèn)題,前蘇聯(lián)的法學(xué)界曾發(fā)生過(guò)一場(chǎng)相當(dāng)激烈的爭(zhēng)論。爭(zhēng)論的結(jié)果是巴舒坎尼斯的觀點(diǎn)占了上風(fēng)。巴氏認(rèn)為,所有的法律都是資產(chǎn)階級(jí)性質(zhì)的,當(dāng)時(shí)的蘇維埃法律也不例外,也是處在不斷消亡之中的法律(注:參見(jiàn)[蘇]維辛斯基:《國(guó)家和法的理論問(wèn)題》,法律出版社1955年版,第90頁(yè);另參見(jiàn)[德]茨威格特等著:《比較法總論》,潘漢典等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16頁(yè)。)。這即是說(shuō),前蘇聯(lián)基于“新經(jīng)濟(jì)政策”之推行而制訂的那些法律,都是不得已而為之的產(chǎn)物。對(duì)此,還有前蘇聯(lián)人的事后評(píng)說(shuō)為證,即“同戰(zhàn)時(shí)共產(chǎn)主義比較,新經(jīng)濟(jì)政策在初期是作了一定限度的退卻。……實(shí)行暫時(shí)退卻的策略,是為了以后轉(zhuǎn)入新的進(jìn)攻”(注:參見(jiàn)《蘇聯(lián)共產(chǎn)黨歷史》(中譯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67 頁(yè)。)。這便表明, 前蘇聯(lián)最初所持的法律虛無(wú)主義治國(guó)觀念是客觀存在之事實(shí)。
但是,到了本世紀(jì)30年代,基于斯大林的明確表態(tài)才使前蘇聯(lián)的法律虛無(wú)主義觀念一掃而光。因?yàn)椋勾罅衷诋?dāng)時(shí)曾多次強(qiáng)調(diào),作為過(guò)渡時(shí)期的蘇聯(lián)既面臨著階級(jí)斗爭(zhēng)日益尖銳的局面(注:參見(jiàn)[蘇]維辛斯基:《國(guó)家和法的理論問(wèn)題》,法律出版社1955年版,第73頁(yè)。),又面臨著維護(hù)國(guó)家所有制的任務(wù)(注:參見(jiàn)北京大學(xué)法律系:《馬、恩、列、斯論民法》,1964年10月,第245頁(yè)。),還肩負(fù)著推行國(guó)民經(jīng)濟(jì)計(jì)劃化的使命(注:參見(jiàn)北京大學(xué)法律系:《馬、恩、列、斯論民法》,1964年10月,第280頁(yè)。),因此不僅需要法律,還需要能夠?qū)α⒂诟鞣N剝削階級(jí)法律類型的社會(huì)主義法律。那么,什么樣的法律才屬于社會(huì)主義性質(zhì)的法律呢?維辛斯基的“意志法”理論便應(yīng)運(yùn)而生了:“法律是表現(xiàn)統(tǒng)治階級(jí)意志、以立法所規(guī)定的行為規(guī)范以及為國(guó)家權(quán)力所認(rèn)可的社會(huì)生活規(guī)范與習(xí)慣的總和。”(注:轉(zhuǎn)引自[德]茨威格特等:《比較法總論》,潘漢典等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17頁(yè)。)維辛斯基的“意志法”理論出現(xiàn)以后,不僅成了社會(huì)主義法本質(zhì)規(guī)定性最具有權(quán)威性的理論概括及定義界定,而且,還為前蘇聯(lián)民法學(xué)界個(gè)別人早就提出的法律行為本質(zhì)合法說(shuō)觀點(diǎn)提供了難能可貴的登臺(tái)亮相機(jī)會(huì)。關(guān)于后一點(diǎn),通過(guò)法律行為本質(zhì)合法說(shuō)觀點(diǎn)在前蘇聯(lián)民法理論中的形成與發(fā)展過(guò)程,我們便會(huì)看得甚為明白。
第二,前蘇聯(lián)的法律行為本質(zhì)合法說(shuō)觀點(diǎn)自始就是一種缺乏確切形成依據(jù)的虛構(gòu)性觀點(diǎn),事實(shí)上也曾為前蘇聯(lián)的民法學(xué)界冷落多時(shí),但是,基于“意志法”理論的出臺(tái),不僅使該種觀點(diǎn)身價(jià)倍增,而且,還一度成為前蘇聯(lián)民法理論中的主導(dǎo)性觀點(diǎn)。
在前蘇聯(lián),有關(guān)法律行為本質(zhì)合法說(shuō)觀點(diǎn)的提出,起因于1922年的蘇俄民法典使用了“無(wú)效法律行為”一詞(注:參見(jiàn)1922年的《蘇俄民法典》,法律出版社1956年版,第9、10頁(yè)。),以及在1929 年時(shí)學(xué)者別列捷爾斯基對(duì)于該語(yǔ)在該法典當(dāng)中的使用所形成的看法。別氏認(rèn)為,無(wú)效的法律行為既然不能產(chǎn)生出行為人預(yù)期的法律后果,便不應(yīng)劃入法律行為的范疇(注:參見(jiàn)[蘇]諾維茨基著:《法律行為·訴訟時(shí)效》,康寶田譯,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1956年版,第69、70頁(yè)。)。嚴(yán)格而論,別氏的這種看法純系無(wú)事生非。因?yàn)椋诜尚袨楦拍钪枢l(xiāng)——德國(guó)民法典上,“法律行為”自始就是一個(gè)種概念,而“無(wú)效法律行為”只是一個(gè)屬概念。由于別氏之看法明顯有悖于 “法律行為”概念界定之基本常識(shí)(注:事實(shí)表明,德國(guó)人賀古所創(chuàng)造的“法律行為”概念,是以古羅馬法之“適法行為”作為基礎(chǔ)的,其內(nèi)涵界定之醞釀自然已有數(shù)千年的歷史,故應(yīng)屬“基本常識(shí)”。參見(jiàn)[意]彼德羅·彭梵得著:《羅馬法教科書(shū)》,黃風(fēng)譯,中國(guó)政法大學(xué)出版社1996年版,第58頁(yè)。),再加上當(dāng)時(shí)的蘇聯(lián)尚處于法律虛無(wú)主義觀念泛濫之際,從而使別氏之“看法”備受冷落。但是,當(dāng)維辛斯基的“意志法”理論出臺(tái)之后,特別是在維辛斯基進(jìn)一步提出“蘇維埃社會(huì)主義民法的基礎(chǔ),不是羅馬法,而是公法原則”的觀點(diǎn)之后(注:[蘇]維辛斯基:《國(guó)家和法的理論問(wèn)題》,法律出版社1955年版,第118頁(yè)。),別氏“看法”的“理論價(jià)值”才得以被人發(fā)現(xiàn),并被派上了大用場(chǎng)。例如,前蘇聯(lián)學(xué)者阿加爾柯夫正是以別氏的看法為基點(diǎn),才明確提出法律行為本質(zhì)合法說(shuō)觀點(diǎn)的(注:[蘇]諾維茨基:《法律行為·訴訟時(shí)效》,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1956年版,第70、71、8頁(yè)。)。
首先,阿加爾柯夫明確主張,俄國(guó)人拉底舒切夫于18世紀(jì)末即已創(chuàng)造出“適法”意義的法律行為概念,并因此而使法律行為的研究在民法總論中獨(dú)立成為俄國(guó)民法學(xué)科的傳統(tǒng)(注:尹田著:《民事法律行為與制度研究》,重慶大學(xué)出版社1993年版,第2頁(yè)。)。阿氏之如此用心,無(wú)非是為了說(shuō)明,法律行為概念的真正故鄉(xiāng)不是德意志而是俄羅斯。但是,阿氏的此種說(shuō)法是沒(méi)有根據(jù)的。因?yàn)椋湟唬砹_斯民族于公元8到9 世紀(jì)時(shí)才擁有國(guó)家(注:陳盛清主編:《外國(guó)法律史》,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1982年版,第119頁(yè)。),18 世紀(jì)的下半葉才有大學(xué)(注:參見(jiàn)[法]勒內(nèi)·達(dá)維德著:《當(dāng)代主要法律體系》,漆竹生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157頁(yè)。)。其民族文化發(fā)展歷史如此之短暫,何以會(huì)醞釀出法律行為概念得以產(chǎn)生的思想與文化條件?其二,拋開(kāi)18世紀(jì)俄國(guó)的實(shí)際情形不論,即使推遲到“19世紀(jì)
中葉,俄國(guó)還存在著農(nóng)奴制度”(注:參見(jiàn)《蘇聯(lián)共產(chǎn)黨歷史》(中譯本), 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7頁(yè)。),而與之相匹配的“政治制度是極權(quán)君主制”(注:參見(jiàn)《蘇聯(lián)共產(chǎn)黨歷史》(中譯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0頁(yè)。),從而表明19世紀(jì)中葉的俄國(guó),基于其低下的經(jīng)濟(jì)與政治水平,也不足以萌生出以個(gè)人自由主義而為法律哲學(xué)底蘊(yùn)的法律行為概念。
阿加爾柯夫認(rèn)為:“法律行為不可能是無(wú)效的,無(wú)效的只可能是人們借以從事法律行為的那個(gè)意思表示”(注:[蘇]諾維茨基:《法律行為·訴訟時(shí)效》,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1956年版,第70、71、8頁(yè)。);因?yàn)椤盁o(wú)效法律行為”一語(yǔ)“是不合邏輯的”(注:[蘇]諾維茨基:《法律行為·訴訟時(shí)效》,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1956年版,第70、71、8頁(yè)。);解決該問(wèn)題的出路即在于,用“法律行為”一語(yǔ)來(lái)表示可產(chǎn)生行為人期待結(jié)果的合法有效行為,而用“意思表示”來(lái)取代傳統(tǒng)意義的法律行為概念(注:[蘇]諾維茨基:《法律行為·訴訟時(shí)效》,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1956年版,第70、71、8頁(yè)。)。但顯而易見(jiàn)的是,一方面,關(guān)于法律行為本質(zhì)屬性合法的確切形成依據(jù)是什么、以及“無(wú)效法律行為”一詞又為什么不合邏輯等諸多問(wèn)題,阿氏均采實(shí)質(zhì)上的有意回避態(tài)度;另一方面,即我國(guó)民事法律行為本質(zhì)合法說(shuō)觀點(diǎn)的始作俑者在提出該種觀點(diǎn)時(shí),完全是照搬了阿氏的上述理論(注:參見(jiàn)《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民法原理》第 168頁(yè), 全國(guó)第三期法律專業(yè)師資班1983年7月整理。)。阿氏對(duì)于自己所主張的法律行為本質(zhì)合法說(shuō)觀點(diǎn),其底氣與信心顯然并不十分充足。因?yàn)椋⑹弦环矫嬲J(rèn)為,對(duì)于當(dāng)時(shí)的蘇維埃法律來(lái)說(shuō),將私法自治作為法律行為的特點(diǎn)是不合適的;另一方面又不能不承認(rèn),私法自治在當(dāng)時(shí)的蘇維埃社會(huì)生活中畢竟尚起一定的作用(注:尹田著:《民事法律行為與制度研究》,重慶大學(xué)出版社1993年版,第11頁(yè)。)。這便表明,法律行為本質(zhì)合法說(shuō)觀點(diǎn)在前蘇聯(lián)自治就是一種沒(méi)有確切形成依據(jù)的虛構(gòu)性觀點(diǎn)。
再次,阿氏的法律行為本質(zhì)合法說(shuō)觀點(diǎn)亮相以后,曾遭到前蘇聯(lián)一些學(xué)者的堅(jiān)決批評(píng)。例如,學(xué)者堅(jiān)金就曾一針見(jiàn)血地指出:“合法或不合法并不是法律行為這一法律事實(shí)的必要特征,而只決定著法律行為的這些或那些后果。”(注:[蘇]諾維茨基:《法律行為·訴訟時(shí)效》,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1956年版,第70、 71、8頁(yè)。)學(xué)者諾維茨基一方面批評(píng)阿氏“把法律行為的法律后果包括在法律行為的事實(shí)構(gòu)成之中”,是“既不正確而又無(wú)意義的”;(注:參見(jiàn)[蘇]諾維茨基:《法律行為·訴訟時(shí)效》,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1956年版,第71頁(yè)。)另一方面則直接以“國(guó)家本位與國(guó)家萬(wàn)能”作為該種觀點(diǎn)的支持依據(jù)。因?yàn)椋Z氏認(rèn)為:合法性之所以是法律行為的特有特征,在于法律行為的內(nèi)容應(yīng)當(dāng)能夠“經(jīng)受得起國(guó)家的檢查和評(píng)定”、以及“應(yīng)與國(guó)家利益相符合”(注:參見(jiàn)[蘇]諾維茨基:《法律行為·訴訟時(shí)效》,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1956年版,第9頁(yè)。)。嚴(yán)格而論,諾氏之闡釋雖有指鹿為馬之破綻(注:諾維茨基將法律行為的“成立”和“有效”混為一談,本身就是一種指鹿為馬。),但也甚為清楚地道出了這樣一個(gè)事實(shí):維辛斯基的“意志法”理論,是使前蘇聯(lián)法律行為本質(zhì)合法說(shuō)觀點(diǎn)得以形成的第一個(gè)實(shí)質(zhì)性支持依據(jù)。較之于阿加爾柯夫,諾維茨基倒是少了若干“羞澀”,而多了幾份“直白”與“坦率”。
最后,前蘇聯(lián)的法律行為本質(zhì)合法說(shuō)觀點(diǎn)之所以能夠得到“意志法”理論的支持,在于前者能夠淋漓盡致地表達(dá)出后者的意旨。因?yàn)椋桃庖蠓尚袨椤氨举|(zhì)合法”,正是為了推行法律行為法定主義(注:參見(jiàn)拙文:《論法律行為的合法與本質(zhì)》,《法律科學(xué)》1998年第5 期。);而如果有了法律行為法定主義,則“意志法”理論的終極性目標(biāo)——“國(guó)家本位”與“國(guó)家萬(wàn)能”就有了實(shí)現(xiàn)的途徑和措施保障。如此說(shuō)來(lái),前蘇聯(lián)的法律行為本質(zhì)合法說(shuō)觀點(diǎn)實(shí)系其“意志法”理論之產(chǎn)物,應(yīng)屬不爭(zhēng)之事實(shí)。
二
事實(shí)表明,發(fā)韌于前蘇聯(lián)的法律行為本質(zhì)合法說(shuō)觀點(diǎn),在構(gòu)成“意志法”理論產(chǎn)物的同時(shí),還是其計(jì)劃經(jīng)濟(jì)體制的產(chǎn)物。因?yàn)椋贤鳛槭袌?chǎng)經(jīng)濟(jì)的產(chǎn)物與工具,原本即與計(jì)劃經(jīng)濟(jì)體制無(wú)緣,但在前蘇聯(lián),為全面改變合同的固有屬性而使之成為計(jì)劃經(jīng)濟(jì)推行的工具,自然需要法律行為本質(zhì)合法說(shuō)理論與觀點(diǎn)的支持。
第一,關(guān)于前蘇聯(lián)對(duì)于合同的態(tài)度,事實(shí)上曾出現(xiàn)過(guò)三次大的變化,即從堅(jiān)決否定到無(wú)可奈何地利用,再到抽去合同的固有本質(zhì)屬性。其中,抽去合同本質(zhì)屬性的態(tài)度確立正是基于計(jì)劃經(jīng)濟(jì)體制推行的需要。
首先,在論及建國(guó)之初的蘇聯(lián)為什么要推行戰(zhàn)時(shí)共產(chǎn)主義政策時(shí),前蘇聯(lián)人的回答通常都是“僅僅為了戰(zhàn)爭(zhēng)”,即“在外國(guó)武裝干涉和國(guó)內(nèi)戰(zhàn)爭(zhēng)的條件下,戰(zhàn)時(shí)共產(chǎn)主義政策是唯一可行的政策,事實(shí)證明它是完全正確的”(注:參見(jiàn)《蘇聯(lián)共產(chǎn)黨歷史》(中譯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20頁(yè)。)。然而,大量的事實(shí)表明,這種馬后炮意義的說(shuō)法并不完全符合當(dāng)時(shí)的實(shí)際情況。因?yàn)椋疤K聯(lián)推行戰(zhàn)時(shí)共產(chǎn)主義政策的目的客觀上有兩個(gè):一是為了戰(zhàn)爭(zhēng);同時(shí)通過(guò)此種政策的實(shí)施而期待著直接、迅速地過(guò)渡到共產(chǎn)主義。正是基于后一目的,才使1918年的俄國(guó)憲法有意識(shí)不用國(guó)家一詞(注:參見(jiàn)[法]勒內(nèi)·達(dá)維德:《當(dāng)代主要法律體系》,漆竹生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174頁(yè)。),才有傳統(tǒng)的合同交易關(guān)系而為國(guó)家的統(tǒng)一分配關(guān)系所取代(注:參見(jiàn)[法]勒內(nèi)·達(dá)維德:《當(dāng)代主要法律體系》,漆竹生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174頁(yè)。),才使當(dāng)時(shí)的人們普遍感覺(jué)到商品與貨幣似乎已屬多余(注:參見(jiàn)[法]勒內(nèi)·達(dá)維德:《當(dāng)代主要法律體系》,漆竹生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174 頁(yè)。),才使法學(xué)家屬于可疑階層而普遍不受信任(注:參見(jiàn)[法]勒內(nèi)·達(dá)維德:《當(dāng)代主要法律體系》,漆竹生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174頁(yè)。)。 ……這便清楚地表明,作為戰(zhàn)時(shí)共產(chǎn)主義政策推行時(shí)的前蘇聯(lián),對(duì)于合同原本是持堅(jiān)決否定態(tài)度的。
其次,20世紀(jì)20年代,前蘇聯(lián)之所以實(shí)施新經(jīng)濟(jì)政策,根本原因是其“國(guó)家的內(nèi)部狀況非常困難”(注:參見(jiàn)《蘇聯(lián)共產(chǎn)黨歷史》(中譯本),人民出版社 1960年版,第356頁(yè)。):一是“1920 年大工業(yè)產(chǎn)值比戰(zhàn)前時(shí)期幾乎減少了6/7”(注:參見(jiàn)《蘇聯(lián)共產(chǎn)黨歷史》(中譯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56頁(yè)。);二是同年的“農(nóng)業(yè)產(chǎn)值只等于沙皇俄國(guó)農(nóng)業(yè)產(chǎn)值的65%”(注:參見(jiàn)《蘇聯(lián)共產(chǎn)黨歷史》(中譯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57、358、356 頁(yè)。);三是“農(nóng)民不滿意余糧收集制”而“起來(lái)舉行暴動(dòng)”(注:參見(jiàn)《蘇聯(lián)共產(chǎn)黨歷史》(中譯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57、358、356頁(yè)。);四是工人“由于饑餓”而“對(duì)蘇維埃政權(quán)的經(jīng)濟(jì)政策表示不滿”并且舉行“罷工”(注:參見(jiàn)《蘇聯(lián)共產(chǎn)黨歷史》(中譯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 357、358、356頁(yè)。);五是因?yàn)椤坝嗉Z收集制”而釀出了“水兵的叛亂”(注:參見(jiàn)《蘇聯(lián)共產(chǎn)黨歷史》(中譯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57、358、356頁(yè)。)。…… 凡此種種都表明了,當(dāng)時(shí)“困難”的形成原因絕非單純只是“帝國(guó)主義戰(zhàn)爭(zhēng)、國(guó)內(nèi)戰(zhàn)爭(zhēng)和外國(guó)武裝干涉”(注:參見(jiàn)《蘇聯(lián)共產(chǎn)黨歷史》(中譯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 357、358、356頁(yè)。),還應(yīng)當(dāng)有以仇視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的民族傳統(tǒng)心理習(xí)慣為基礎(chǔ)(注:據(jù)說(shuō),俄羅斯文學(xué)家列夫·托爾斯泰曾兩度到歐州發(fā)達(dá)國(guó)家考察,通過(guò)考察而感受到,還是俄國(guó)傳統(tǒng)的以農(nóng)耕為社會(huì)的主要生產(chǎn)方式、以“德治”為社會(huì)管理主要手段的“自由平等”的小農(nóng)社會(huì)遠(yuǎn)遠(yuǎn)優(yōu)越于那些以工商
業(yè)為基礎(chǔ)的“法治”社會(huì)。托氏被譽(yù)為“俄國(guó)革命的鏡子”的緣由似乎亦在于此,可知俄羅斯民族對(duì)于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亦有著相當(dāng)深厚的仇視心理習(xí)慣。參見(jiàn)《簡(jiǎn)明社會(huì)科學(xué)辭典》,上海辭書(shū)出版社1982年版,第305 頁(yè);另見(jiàn)《辭海·縮印本》,上海辭書(shū)出版社1980 年版,第665頁(yè)。)、以肆意并人為取締合同的作用而為手段、旨在追求一朝一夕即達(dá)共產(chǎn)主義的那些政策、方針和路線。如此說(shuō)來(lái),新經(jīng)濟(jì)政策的實(shí)施本應(yīng)以承認(rèn)市場(chǎng)的客觀存在,承認(rèn)合同作用的社會(huì)規(guī)律性質(zhì)為基本內(nèi)容。但是,事實(shí)表明,前蘇聯(lián)基于新經(jīng)濟(jì)政策之實(shí)施而起用合同,純粹是出于迫不得已,并且只是把合同作為一種工具而暫時(shí)利用罷了,對(duì)于合同所持的否定態(tài)度則絲毫沒(méi)有改變。
再次,伴隨著新經(jīng)濟(jì)政策的實(shí)施終止,前蘇聯(lián)便逐步進(jìn)入到計(jì)劃經(jīng)濟(jì)的時(shí)代。為了滿足計(jì)劃經(jīng)濟(jì)體制全面深入推行的需要,前蘇聯(lián)才對(duì)自己堅(jiān)決否定合同的一貫態(tài)度與立場(chǎng),進(jìn)行了極其耐人尋味的調(diào)整與改變。這種調(diào)整與改變的事實(shí)集中于下列幾點(diǎn):一是不僅不再否定和排斥合同,而且,賦予合同以貫徹落實(shí)經(jīng)濟(jì)計(jì)劃工具的使命并因此而大加提倡與推崇。這是因?yàn)椋诋?dāng)時(shí)的蘇聯(lián)人看來(lái),一方面,“合同聯(lián)系的制度,乃是經(jīng)濟(jì)計(jì)劃與經(jīng)濟(jì)核算原則相結(jié)合的最好辦法,所以一切經(jīng)濟(jì)組織應(yīng)對(duì)這件事情予以特別注意”(注:參見(jiàn)[蘇]赫魯菲娜著:《蘇維埃社會(huì)主義民法中合同的意義和本質(zhì)》,鄧華等譯,法律出版社1956年版,第11頁(yè)。);另一方面,即“在實(shí)際上把計(jì)劃同合同有害地對(duì)立起來(lái)和認(rèn)為有了計(jì)劃就不需要合同的觀點(diǎn),都是不能容許的”(注:參見(jiàn)[蘇]赫魯菲娜著:《蘇維埃社會(huì)主義民法中合同的意義和本質(zhì)》,鄧華等譯,法律出版社1956年版,第16頁(yè)。)。顯而易見(jiàn)的是,之所以以禁令的方式宣稱“不容許把計(jì)劃同合同對(duì)立起來(lái)”的目的,正是為了使人們對(duì)此二者之間的客觀對(duì)立關(guān)系或者“視而不見(jiàn)”或者“保持沉默”;二是受上述特定目的之支配,則有必要徹底抽去合同的固有屬性,亦即前蘇聯(lián)人所直言不諱的:“在我們的條件下,……把舊的東西自己的本性改變得與新的東西相適應(yīng),僅僅保持著自己的形式;至于新的東西是滲透到舊的東西里面去,并不破壞它的形式,而是利用它來(lái)求自己的發(fā)展”(注:參見(jiàn)[蘇]赫魯菲娜著:《蘇維埃社會(huì)主義民法中合同的意義和本質(zhì)》,鄧華等譯,法律出版社1956年版,第 9頁(yè)。)。這便清楚表明,正是緣于那些虛構(gòu)出來(lái)的所謂目標(biāo),才使前蘇聯(lián)人只能依靠公然的“偷梁換柱”而別無(wú)他種辦法;三是以粉飾上述行徑為目的,抬出了“統(tǒng)治階級(jí)意志”既作為公、私法劃分客觀標(biāo)準(zhǔn)與理論的替代物,同時(shí)又作為顛倒法律與社會(huì)存在二者之間原有關(guān)系的理論根據(jù)。前蘇聯(lián)學(xué)者斯圖契卡正是依據(jù)“法乃統(tǒng)治階級(jí)意志,故公法與私法劃分不能成立”這一典型“抬杠”式的說(shuō)教,提出至今尚無(wú)人能夠說(shuō)得清楚的所謂的“經(jīng)濟(jì)法部門”理論,并企圖以此將民法取而代之(注:參見(jiàn)[蘇]維辛斯基:《國(guó)家和法的理論問(wèn)題》,法律出版社1955年版,第93頁(yè)。);赫魯菲娜則說(shuō)得極為明白:“應(yīng)該了解個(gè)別法律部門的法律制度與社會(huì)的政治、法律、哲學(xué)和其它觀點(diǎn)相適合,所以經(jīng)濟(jì)關(guān)系并不是直接的,而是通過(guò)統(tǒng)治階級(jí)的意志來(lái)決定這種制度”(注:參見(jiàn)[蘇]赫魯菲娜著:《蘇維埃社會(huì)主義民法中合同的意義和本質(zhì)》,法律出版社1956年版,第10、6、10頁(yè)。)。但是在這里,赫氏卻犯了一個(gè)常識(shí)性的錯(cuò)誤,那就是作為“統(tǒng)治階級(jí)”通過(guò)自己的 “意志”而反映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存在時(shí),事實(shí)上就既有“真實(shí)”的可能,亦有“失真”乃至“造假”的可能。由此即知,赫氏所欲追求的正是“本末倒置”技法的效應(yīng)。
還應(yīng)當(dāng)看到的是,雖有上述諸多“措施”的采取,但相對(duì)于合同需要充當(dāng)經(jīng)濟(jì)計(jì)劃工具的意圖而言似乎還有一定的距離。因?yàn)椋贤揪褪敲穹ㄉ系姆懂牐匀贿€需要有一種特別的民法理論而對(duì)此種意圖作出富于“民法專業(yè)”色彩的說(shuō)明及解釋(注:這是因?yàn)槲闹兴械摹岸氯酥凇薄巴盗簱Q柱”、“本末倒置”等措施,均非民法的“行內(nèi)之舉”,故無(wú)從具備民法的專業(yè)色彩。)。而這種特別的民法理論,顯然又非前蘇聯(lián)學(xué)者阿加爾柯夫的法律行為本質(zhì)合法說(shuō)莫屬了。
第二,正是因?yàn)閾碛辛朔尚袨楸举|(zhì)合法說(shuō)的理論觀點(diǎn),才使前蘇聯(lián)人甚為“內(nèi)行”地抽去了合同的固有本質(zhì)屬性,并使將合同充作計(jì)劃經(jīng)濟(jì)推行工具的設(shè)想變成了一種現(xiàn)實(shí),進(jìn)而說(shuō)明該項(xiàng)理論觀點(diǎn)天生就是前蘇聯(lián)計(jì)劃經(jīng)濟(jì)體制的產(chǎn)物。
關(guān)于前蘇聯(lián)人憑借于法律行為本質(zhì)合法說(shuō)的觀點(diǎn)而抽去合同的固有本質(zhì)屬性,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幾個(gè)方面:
首先,從合同(契約)概念沿革以及合同與債之間關(guān)系演進(jìn)的史實(shí)可知,一方面,合同實(shí)乃雙方或方的法律行為,然法律行為的固有本質(zhì)屬性又是行為人不“違法”的個(gè)人自由主義,從而使合同之理念對(duì)之于政治和哲學(xué)以個(gè)人自由主義為限定,對(duì)之于法律制度以權(quán)利本位為限定(注:參見(jiàn)拙文:《論法律行為的合法與本質(zhì)》,《法律科學(xué)》1998年第5期。)。這是合同不能充作計(jì)劃經(jīng)濟(jì)推行工具的根本性障礙;另一方面,合同屬債的范疇,故還有一種非本質(zhì)意義的屬性亦即“法鎖”的性質(zhì)。這便表明,前蘇聯(lián)人之所以選擇合同充當(dāng)計(jì)劃經(jīng)濟(jì)的工具,顯然只是鐘情于合同的 “法鎖”作用,以及借此機(jī)會(huì)還可剪除合同的權(quán)利本位。受此“一石二鳥(niǎo)”動(dòng)機(jī)的驅(qū)使,前蘇聯(lián)人雖未公開(kāi)宣稱合同應(yīng)當(dāng)以義務(wù)為本位,但卻以法律行為本質(zhì)合法說(shuō)的觀點(diǎn)(注:法律行為本質(zhì)合法說(shuō)觀點(diǎn)就是要將義務(wù)本位強(qiáng)加在法律行為頭上。參見(jiàn)拙文:《論法律行為的合法與本質(zhì)》,《法律科學(xué)》1998年第5期。),以及“計(jì)劃是合同義務(wù)的基礎(chǔ)”之口號(hào)為依據(jù)(注:參見(jiàn)[蘇]赫魯菲娜著:《蘇維埃社會(huì)主義民法中合同的意義和本質(zhì)》,法律出版社1956年版,第10、 6、10頁(yè)。),通過(guò)“繞彎子”的方式而將義務(wù)本位的“政策法”負(fù)擔(dān)強(qiáng)加在合同的頭上。這樣以來(lái),前蘇聯(lián)人的目的顯然已經(jīng)達(dá)到。因?yàn)椋?jì)劃倘若作為合同義務(wù)的基礎(chǔ),則合同主體所負(fù)的義務(wù)至少就有四項(xiàng):一是受計(jì)劃之指令而必須締約;二是必須與計(jì)劃所指定的相對(duì)人締約;三是合同的內(nèi)容必須由計(jì)劃來(lái)決定;四是必須實(shí)際履行合同。換言之,通過(guò)合同而貫徹執(zhí)行計(jì)劃自然就暢通無(wú)阻。
其次,關(guān)于計(jì)劃合同的主體,前蘇聯(lián)人曾以“社會(huì)主義組織”一語(yǔ)而名之。然其之所以選用該語(yǔ),顯然又是為了達(dá)到以下幾項(xiàng)目的:一是選用該語(yǔ),本身即有混淆社會(huì)組織或可成為法律關(guān)系之主體,或只構(gòu)成法律關(guān)系之客體的固有區(qū)別界線的作用,從而便可將一切社會(huì)組織無(wú)一例外地變成經(jīng)濟(jì)計(jì)劃之網(wǎng)的網(wǎng)上紐結(jié)而受國(guó)家的嚴(yán)格控制。因?yàn)椋撜Z(yǔ)雖非法律范疇,然其外延卻極為寬泛:既包括“人的集合”組織,又包括“物的集合”組織;既包括營(yíng)利性的“企業(yè)”實(shí)體,又包括以追求社會(huì)公共福利而為宗旨的“事業(yè)”單位;……這樣以來(lái),不僅會(huì)使一切社會(huì)組織不能不以服從國(guó)家計(jì)劃的支使與安排為要?jiǎng)?wù),而且,亦會(huì)使國(guó)有企業(yè)這一原本即系國(guó)家所有權(quán)的客體一躍而成為計(jì)劃合同的主體,最終還能將國(guó)家的“東家”身份掩蓋起來(lái)(注:大量事實(shí)表明,基于商品經(jīng)濟(jì)以及國(guó)家所有制的客觀存在,遂使國(guó)家資本主義并非像有些人所講的那樣,僅系一朝一夕的權(quán)宜之計(jì),相反,倒是一種持續(xù)性質(zhì)的現(xiàn)象。因此,國(guó)家的“商人”面目與其“老板”的身份并不能夠從社會(huì)生活事實(shí)中抹去。)。但是,前蘇聯(lián)人的此一作為畢竟又屬“以紙包火”,遲早都會(huì)露餡的;二是基于該語(yǔ)的選用,還可對(duì)計(jì)劃合同主體的法律地位和人格,或采之以含糊其辭的回避說(shuō)法,或采之以公然的否定態(tài)度。例如,前蘇聯(lián)學(xué)者赫魯菲娜就曾明確談到:“在蘇維埃著作里不準(zhǔn)使用法人人格化,不準(zhǔn)把只能適用于公民,適用于活著的人的那樣的概念和范疇也適用于法人。”(注:參見(jiàn)[蘇]赫魯菲娜:《蘇維埃社會(huì)主義民法中合同的意義和本質(zhì)》,法律出版社1956年版,第13、14、 21頁(yè)。)這便清楚表明,依據(jù)前蘇聯(lián)人的“用心”,所謂的“社會(huì)主義組織”自始就非計(jì)劃合同的“主體”,相反,倒是操持于國(guó)家股掌之上的工具和機(jī)器;而其既將該類組織在充作計(jì)劃合同“主體”的同時(shí),又公然否認(rèn)其主體人格的行徑,無(wú)疑又是因受到法律行為本質(zhì)合法說(shuō)觀點(diǎn)的“技術(shù)啟發(fā)”之后才得以實(shí)施的。但是,事實(shí)表明,前蘇聯(lián)人的此類“長(zhǎng)袖善舞”,既存在著“成亦蕭何敗亦蕭何”的自相矛盾,還存在著“翻手為云、覆手為雨”的無(wú)常滑稽。
再次,既然那些“社會(huì)主義組織”一個(gè)個(gè)都是國(guó)家用于推行經(jīng)濟(jì)計(jì)劃的工具與機(jī)器,那么,對(duì)于他們既有必要經(jīng)常性地加注一些旨在促使此種機(jī)器能夠正常運(yùn)作的潤(rùn)滑劑——“企業(yè)經(jīng)理基金”(注:參見(jiàn)[蘇]赫魯菲娜:《蘇維埃社會(huì)主義民法中合同的意義和本質(zhì)》,法律出版社1956年版,第13、14、21頁(yè)。),尤有必要對(duì)于他們執(zhí)行計(jì)劃的行為實(shí)行所謂的“全面監(jiān)督(注:參見(jiàn)[蘇]赫魯菲娜:《蘇維埃社會(huì)主義民法中合同的意義和本質(zhì)》,法律出版社1956年版,第 13、14、21頁(yè)。)。作為監(jiān)督者,不僅有計(jì)劃合同的相對(duì)人,還有黨的組織、社會(huì)團(tuán)體、行政機(jī)關(guān)、經(jīng)濟(jì)機(jī)關(guān)乃至不特定的公民個(gè)人(注:參見(jiàn)[蘇]赫魯菲娜:《蘇維埃社會(huì)主義民法中合同的意義和本質(zhì)》,法律出版社1956年版,第13、14、21頁(yè)。);作為監(jiān)督的方式,則既有法律的,又有行政的,還有社會(huì)輿論的(注:參見(jiàn)[蘇]赫魯菲娜:《蘇維埃社會(huì)主義民法中合同的意義和本質(zhì)》,法律出版社1956年版,第13、14、21頁(yè)。)。而如此之”法網(wǎng)恢恢“,無(wú)非是為了使那些計(jì)劃合同”主體“,不敢越出計(jì)劃合同義務(wù)本位”雷池“一步。這表明,”全面監(jiān)督“之種種舉措,正是因?yàn)閾碛辛朔尚袨楸举|(zhì)合法說(shuō)觀點(diǎn)的”技術(shù)幫助“始得”自圓其說(shuō)“的;同時(shí),法律行為本質(zhì)合法說(shuō)觀點(diǎn)實(shí)乃計(jì)劃經(jīng)濟(jì)體制之產(chǎn)物,確系不爭(zhēng)之事實(shí)。
第三,無(wú)論是前蘇聯(lián)人“意志法”理論所稱的“法”,擬或是其曾經(jīng)推行過(guò)的經(jīng)濟(jì)計(jì)劃,事實(shí)上原本就是一回事,即都是以旨在樹(shù)立“國(guó)家本位與國(guó)家萬(wàn)能主義”的信念為最高目標(biāo)而形成的前蘇聯(lián)國(guó)家的“統(tǒng)治階級(jí)意志”。這既是“意志法”理論與計(jì)劃經(jīng)濟(jì)體制的相通和相同之處,同時(shí),也是法律行為本質(zhì)合法說(shuō)觀點(diǎn)之所以會(huì)成為上述二者產(chǎn)物的原因所在。對(duì)此,我們顯然已無(wú)贅述之必要。
三
前已述及,我們考察法律行為本質(zhì)合法說(shuō)觀點(diǎn)的歷史源流,分析并搜尋出促使該種觀點(diǎn)得以形成、維持的社會(huì)意識(shí)形態(tài)(我們通常稱為“政治與經(jīng)濟(jì)”)根源(注:傳統(tǒng)社會(huì)主義條件下的社會(huì)政治與經(jīng)濟(jì),由于都是“統(tǒng)治階級(jí)意志”的產(chǎn)物,故無(wú)從形成質(zhì)的區(qū)別,應(yīng)歸之于意識(shí)形態(tài)的范疇。),目的在于正本清源、撥亂反正,徹底否定該種觀點(diǎn)。因?yàn)槭聦?shí)表明,倘若容許該種觀點(diǎn)繼續(xù)存在,不僅有礙于中國(guó)改革開(kāi)放大政的繼續(xù)推進(jìn),亦有礙于社會(huì)主義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體制目標(biāo)在中國(guó)的如期建立;不僅有礙于中國(guó)法制現(xiàn)代化建設(shè)的順利完成,更有礙于中華民族振興偉業(yè)的不斷發(fā)展。但是,還應(yīng)當(dāng)看到的是,一方面,即基于中國(guó)改革開(kāi)放的實(shí)際需要而為鄧小平同志率先倡導(dǎo)的“撥亂反正”(注:參見(jiàn)《鄧小平文選》,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1頁(yè)。),事實(shí)上已經(jīng)成為我們所面臨的一項(xiàng)長(zhǎng)期而又艱巨的工作任務(wù);另一方面,中國(guó)已經(jīng)將社會(huì)主義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體制作為自己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目標(biāo),并因此而宣告了計(jì)劃經(jīng)濟(jì)體制在中國(guó)的終結(jié)。鑒于此,我們討論的重點(diǎn)亦有必要轉(zhuǎn)移到 “意志法”的理論上來(lái)。
有資料表明,早在20世紀(jì)的60年代之初,伴隨著赫魯曉夫所進(jìn)行的社會(huì)主義改革嘗試,當(dāng)時(shí)的蘇聯(lián)人不僅明確提出過(guò)“全民國(guó)家全民黨”以及“全民法”的口號(hào),而且,還對(duì)“意志法”理論進(jìn)行過(guò)反思與批判,并因此而形成了若干項(xiàng)頗有價(jià)值的理論觀點(diǎn)。例如,彼昂特考夫斯基就曾明確談及,維辛斯基的“法的概念沒(méi)有指出法律規(guī)范是由社會(huì)的物質(zhì)生活條件所決定的,這就為唯意志論在法的創(chuàng)制中打開(kāi)了方便之門,在制定蘇維埃立法時(shí)企圖忽視社會(huì)主義社會(huì)發(fā)展的客觀規(guī)律。…… 定義中的錯(cuò)誤還在于過(guò)高估價(jià)作為保障適用法律規(guī)范手段的國(guó)家強(qiáng)制力”(注:參見(jiàn)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法學(xué)研究所編:《蘇聯(lián)“全民法”問(wèn)題文摘》,法律出版社 1965年版,第35頁(yè)。);而阿歷山大羅夫更是明確指出:“在斯大林個(gè)人迷信的年代中,維辛斯基充當(dāng)了斯大林在國(guó)家和法的理論領(lǐng)域中的喉舌,他從斯大林關(guān)于社會(huì)主義勝利后階級(jí)斗爭(zhēng)尖銳化的錯(cuò)誤和有害的觀點(diǎn)出發(fā),千方百計(jì)企圖使法律科學(xué)為大規(guī)模地鎮(zhèn)壓和違反法制的現(xiàn)象辯護(hù)”(注:參見(jiàn)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法學(xué)研究所編:《蘇聯(lián)“全民法”問(wèn)題文摘》,法律出版社1965年版,第17頁(yè)。)。……當(dāng)然,由于受當(dāng)時(shí)歷史條件的限制,前蘇聯(lián)人對(duì)于“意志法”理論的批判,既不可能從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規(guī)律的立場(chǎng)出發(fā),更不可能超越與沖破“國(guó)家本位與國(guó)家萬(wàn)能主義”神話的羈絆,因而使此次批判既不徹底亦不全面。但是,事實(shí)表明,在中國(guó),時(shí)至今日,“意志法”理論仍然占據(jù)著相當(dāng)大的一塊領(lǐng)地,并事實(shí)上已成為中國(guó)法制現(xiàn)代化的最大理論障礙。因此,考慮到本文篇幅的限制,在此僅將我們對(duì)“意志法”理論的批判性看法簡(jiǎn)要羅列如下:
第一,實(shí)際上“法是統(tǒng)治階級(jí)意志”僅僅是馬克思主義的創(chuàng)始人用于揭露和批判資本主義社會(huì)早期法制局限性的一種理論武器,而非對(duì)社會(huì)主義的法所作的本質(zhì)概括或定義界定。這是因?yàn)椋菏紫龋隈R克思所創(chuàng)立的全部理論當(dāng)中,共產(chǎn)主義乃“自由人”的聯(lián)合且沒(méi)有國(guó)家與法律是有明確結(jié)論的,而從資本主義向共產(chǎn)主義的過(guò)渡時(shí)期——社會(huì)主義社會(huì),馬克思只是提出要建立無(wú)產(chǎn)階級(jí)專政,并沒(méi)有談及要不要法律以及無(wú)產(chǎn)階級(jí)專政如何消亡等問(wèn)題,因此表明馬克思主義法律理論在價(jià)值選擇方面的直接追求,不是為了“社會(huì)主義”的“立”,而是為了“資本主義”的“破”;其次,馬克思主義法律理論的該種旨趣與特點(diǎn)還集中地表現(xiàn)在,每當(dāng)馬克思施放“法是統(tǒng)治階級(jí)意志”這枝“矢”的時(shí)候,總是以資本主義社會(huì)的早期法制而為“的”的,從而表明“法是統(tǒng)治階級(jí)意志”,僅僅是馬克思用于揭露和批判資產(chǎn)階級(jí)早期法制局限性的一種理論武器;再次,基于以上兩點(diǎn)即已更加清楚地表明,前蘇聯(lián)“意志法”理論的始作俑者純粹是從某種實(shí)用主義的立場(chǎng)出發(fā),以斷章取義的方式,截取馬克思著述的只言片語(yǔ),用以作為兜售其“意志法”理論的標(biāo)簽,因此,這既構(gòu)成對(duì)馬克思主義的一種嚴(yán)重歪曲,亦是對(duì)馬克思主義的玷污與褻瀆。
第二,緣于“意志法”理論的指導(dǎo)所造成的最大惡果客觀上有兩項(xiàng),一是該種理論在實(shí)踐層面上曾經(jīng)使社會(huì)主義“封建化”,二是該種理論在理論層面上又曾經(jīng)使馬克思主義“封建化”(注:“封建化”乃李澤厚先生用語(yǔ),參見(jiàn)其著《走自己的路》,安徽文藝出版社1994年版第277、287頁(yè)。):首先,在馬克思的著述當(dāng)中,馬克思曾經(jīng)不止一次地告誡過(guò)人們,無(wú)產(chǎn)階級(jí)在同資產(chǎn)階級(jí)進(jìn)行斗爭(zhēng)的過(guò)程中,無(wú)產(chǎn)階級(jí)在用共產(chǎn)主義取代資本主義的整個(gè)歷史進(jìn)程中,千萬(wàn)不能以封建主義作為自己的斗爭(zhēng)武器(注:參見(jiàn)《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4頁(y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7、678頁(yè)。),否則不但打不倒資產(chǎn)階級(jí),還有可能把自己打倒。但是,發(fā)生在前蘇聯(lián)的并且是由斯大林一手操縱的“大清洗”,以及發(fā)生在中國(guó)的同樣是由所一手導(dǎo)演的“文化革命”,無(wú)一不是從“意志法” 理論的立場(chǎng)出發(fā),并打著社會(huì)主義的旗號(hào)推行封建主義的。而諸如此類的例子,無(wú)論是在解體以前的蘇聯(lián),或者是在改革開(kāi)放以前的中國(guó),似乎并不以該兩例為限。因此,應(yīng)當(dāng)說(shuō),“意志法”理論的形成與存在,確系使社會(huì)主義曾經(jīng)封建化的一個(gè)重要原因;其次,關(guān)于“意志法”理論亦曾使馬克思主義封建化的事實(shí),似乎以如下幾個(gè)理論話題中始終存在著無(wú)從化解之邏輯死結(jié)而為依據(jù):一是如果說(shuō)“法是統(tǒng)治階級(jí)意志”確系馬克思主義創(chuàng)始人專為社會(huì)主義的“法”所下的定義,那么,以 “統(tǒng)治階級(jí)意志”為本質(zhì)規(guī)定的社會(huì)主義的“法”,與流傳于中國(guó)好幾千年的“朕即國(guó)家朕即法”的封建主義
的“法”,又會(huì)有什么區(qū)別呢?二是如果說(shuō)“權(quán)力本位”與“權(quán)力萬(wàn)能”原本就是封建主義的意識(shí)形態(tài)以及其在社會(huì)上層建筑領(lǐng)域當(dāng)中的產(chǎn)物,那么,貼著馬克思主義標(biāo)簽的“意志法”理論,所宣揚(yáng)的不正是“法自權(quán)出”、“權(quán)大于法”以及“權(quán)力本位和萬(wàn)能”的思想和老調(diào)嗎?三是基于中國(guó)封建制度的演進(jìn)歷史人們可知,正是由于封建主義的“法”原本就是皇帝或君主隨心所欲的“意志”,因之,韓非進(jìn)諫于秦始皇兼而用之的“權(quán)、術(shù)、勢(shì)”等諸多“陽(yáng)謀”(注:大量的事實(shí)表明,在中國(guó),“陽(yáng)謀”與“陰謀”區(qū)分的實(shí)質(zhì)標(biāo)準(zhǔn)是“謀者”的名份不同。有君位或擁有權(quán)力而所實(shí)施的“權(quán)謀”謂之“陽(yáng)謀”。),在中國(guó)數(shù)千年的封建社會(huì)中一直都是其“法”的有機(jī)內(nèi)容。對(duì)此,作為社會(huì)主義社會(huì)的 “統(tǒng)治階級(jí)”,又有何種有效措施而能夠?qū)⒋说冉y(tǒng)治術(shù)從社會(huì)主義“法”中排除出去呢?而包含了此等統(tǒng)治術(shù)的“法”還會(huì)優(yōu)越于“法律至上”目標(biāo)指導(dǎo)之下的法制嗎?憑借此種“法制”武器,還能承擔(dān)起既解放全人類同時(shí)又解放自己的歷史使命嗎?……顯而易見(jiàn),“意志法”理論的存在,確曾使馬克思主義封建化實(shí)系不爭(zhēng)之事實(shí)。
第三,在法學(xué)層面上,“意志法”理論顯然是直接違背法的一般常識(shí)的產(chǎn)物,而在哲學(xué)層面上,“意志法”理論無(wú)疑早就成為“真理——實(shí)踐”標(biāo)準(zhǔn),這一哲學(xué)科學(xué)理論命題的絕對(duì)對(duì)立物。這是因?yàn)椋紫龋祟惿鐣?huì)的法律生活實(shí)踐一再表明,關(guān)于法的存在,始終都有“實(shí)然”與“應(yīng)然”兩種狀態(tài)的區(qū)分。作為“實(shí)然”狀態(tài)的法,確實(shí)是立法者“意志”的表現(xiàn)。對(duì)此,規(guī)范分析法學(xué)派的開(kāi)山鼻祖奧斯丁很早就曾看到和談到(注:參見(jiàn)[英]戴維·m·沃克編:《牛津法律大辭典》,鄧正來(lái)等譯,光明日?qǐng)?bào)出版社1988年版,第39頁(yè)。)。但是,同“實(shí)然”狀態(tài)的法相比較,“應(yīng)然”狀態(tài)的法無(wú)疑又是法的根本。因?yàn)椋^的“應(yīng)然”狀態(tài)的法本身就是人類社會(huì)發(fā)展到一定階段時(shí),基于各種原生條件的限制特別是物質(zhì)生活條件的限制所形成的一種自在意義的社會(huì)規(guī)律;其次,正是因?yàn)椤皯?yīng)然”狀態(tài)的法乃法的根本,因之,一方面,在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學(xué)說(shuō)當(dāng)中,即使馬克思是以批判的口吻指出資產(chǎn)階級(jí)的早期法制實(shí)質(zhì)是資產(chǎn)階級(jí)一個(gè)階級(jí)意志的表現(xiàn),但馬克思并沒(méi)有忘記告訴人們,這種意志仍然是由資產(chǎn)階級(jí)所擁有的物質(zhì)生活條件所決定的(注:參見(jiàn)《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8、9頁(yè)。);另一方面,在法學(xué)層面上,又使“善法是法、惡法不是法”的法學(xué)命題很早即為人們所掌握;第三,在哲學(xué)層面上,亦使“實(shí)踐是檢驗(yàn)真理的唯一標(biāo)準(zhǔn)”本身亦成為放之四海而皆準(zhǔn)的真理;第四,在近百年的社會(huì)主義探索實(shí)踐方面,還使那些以“權(quán)力萬(wàn)能”為精神寄托、無(wú)視客觀規(guī)律的存在而肆意妄為的人四處碰壁。這便清楚表明,“意志法”理論將法的本質(zhì)僅僅歸結(jié)為 “統(tǒng)治階級(jí)意志”,顯然是一種極為淺薄的理論說(shuō)教。
第四,中國(guó)改革開(kāi)放的實(shí)踐早就表明,“意志法”理論自始就是中國(guó)法制現(xiàn)代化的最大理論障礙,故基于改革開(kāi)放事業(yè)發(fā)展的實(shí)際需要而有拋棄此種理論的絕對(duì)必要。這是因?yàn)椋紫龋袊?guó)實(shí)行改革開(kāi)放的終極性目標(biāo)是為了實(shí)現(xiàn)中華民族的現(xiàn)代化,而中國(guó)的法制現(xiàn)代化本身就是中華民族現(xiàn)代化的一項(xiàng)有機(jī)構(gòu)成。作為中國(guó)的法制現(xiàn)代化,其具體標(biāo)志客觀上自然會(huì)有很多,然其中的兩項(xiàng)顯然遠(yuǎn)非其它諸項(xiàng)可比而居于絕對(duì)重要的地位:一是作為中國(guó)依法治國(guó)的“法”,必須趨向于“善法”的方向而非“惡法”的選擇;二是中國(guó)既已循之于依法治國(guó)之道,則逐漸實(shí)現(xiàn)“法律至上”的目標(biāo)選擇亦系一種歷史的必然。換言之,前者是指中國(guó)立法的“質(zhì)量”以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體制目標(biāo)為依據(jù)而必須提高;后者又是指普遍存在于國(guó)人中間的、“只相信權(quán)力而不信法”的傳統(tǒng)心里積淀必須得到徹底改變。但是,誠(chéng)如前述,“意志法”理論的存在,不僅會(huì)使中國(guó)的立法時(shí)刻都有“惡法”化的可能,而且,基于其一味宣揚(yáng)“權(quán)大于法”的理論情趣,還使該種理論無(wú)從不成為“法律至上”的對(duì)立物;其次,事實(shí)還表明,中國(guó)落后的總根源既在于中國(guó)一貫以農(nóng)耕為社會(huì)主要生產(chǎn)方式,又在于中國(guó)的封建文化特別發(fā)達(dá),更在于“國(guó)家本位與國(guó)家萬(wàn)能”的思想在中國(guó)根深蒂固。因此,鄧小平同志才將中國(guó)當(dāng)代的改革稱之為“革命”(注:參見(jiàn)《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第113頁(yè)。)。而作為這場(chǎng)革命的對(duì)象,無(wú)疑既有經(jīng)濟(jì)領(lǐng)域當(dāng)中的生產(chǎn)方式落后,又有上層建筑領(lǐng)域當(dāng)中的封建文化成份,以及該種文化之挽歌——“意志法”理論。一言一蔽之,否定并拋棄“意志法”理論及法律行為本質(zhì)合法說(shuō)觀點(diǎn),實(shí)乃中國(guó)社會(huì)進(jìn)化與發(fā)展的一種歷史之必然。
高在敏
[摘要] 我國(guó)《民法通則》將民事法律行為界定為合法行為是理論上的一個(gè)失誤,它導(dǎo)致了民法學(xué)理論的沖突和認(rèn)識(shí)的混亂,也違背了邏輯規(guī)則。應(yīng)該對(duì)民事法律行為概念重新認(rèn)識(shí)。合法性并非民事法律行為的本質(zhì)特征、必備要素和成立要件,只能把合法性作為國(guó)家對(duì)當(dāng)事人民事法律行為的法律評(píng)價(jià)和法律控制的生效要件來(lái)對(duì)待。意思表示才是民事法律行為的優(yōu)秀要素和本質(zhì)特征。在現(xiàn)代社會(huì)主義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體制的建立階段,強(qiáng)調(diào)民事法律行為的意思表示要素具有重要的現(xiàn)實(shí)意義,它有利于激發(fā)民事主體的積極性和創(chuàng)造性,符合現(xiàn)代法治的基本精神。而取消民事法律行為的合法性要件是現(xiàn)代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發(fā)展和人類認(rèn)識(shí)發(fā)展相統(tǒng)一的必然結(jié)果。
[關(guān)鍵詞] 民法通則 民事法律行為 合法性 意思表示
民事法律行為制度是民法學(xué)理論的一項(xiàng)基本內(nèi)容,它是聯(lián)結(jié)權(quán)利主體制度、物權(quán)制度、債權(quán)制度這三大民法理論的紐帶;是客觀權(quán)利義務(wù)向主觀權(quán)利義務(wù)跨越的橋梁;是法制度向法現(xiàn)實(shí)轉(zhuǎn)化的接口。民事法律行為是商品經(jīng)濟(jì)的產(chǎn)物,是人們應(yīng)商品經(jīng)濟(jì)發(fā)展規(guī)范化、簡(jiǎn)約化的要求,而對(duì)紛繁復(fù)雜的各種具體的商品生產(chǎn)和商品交換行為進(jìn)行的抽象和概括。可以說(shuō)每一項(xiàng)民法基本精神的實(shí)現(xiàn),社會(huì)主義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新秩序的建立,無(wú)一不依賴于民事法律行為作用的發(fā)揮。所以對(duì)民事法律行為制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shí)踐意義。本文擬從民事法律行為的根本特征人手,來(lái)探討民事法律行為的確切含義。
一、現(xiàn)行民事法律行為制度立法的誤區(qū)
考察民事法律行為概念的歷史沿革,可以知道,民事法律行為原稱為法律行為,起源于德國(guó)法學(xué)家賀古(又譯胡果)所著的《日耳曼普通法》一書(shū)中。法律行為在德語(yǔ)中是Rechtsgesch?ft,由"Recht"和"Gesch?ft"組合而成,其中"Gesch?ft"是“行為”的意思,“Recht”指“法”、“法律”,同時(shí)兼有“公平”、“合法”之意,只是日本學(xué)者借用漢字中的“法律”和“行為”二詞,將“Rechtsgesch?ft”譯為了”法律行為”。[1]因此,法律行為原有意義含有合法性。既為合法表意行為,這在邏輯上顯然存在著矛盾,于是引起了民事法律行為是否以合法性為要件的爭(zhēng)論,學(xué)說(shuō)理論莫衷一是。為了解決這一矛盾,《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民法通則》(以下簡(jiǎn)稱《民法通則》)在立法上,一方面肯定了民事法律行為專指合法行為,一方面特創(chuàng)“民事行為”這一新概念,從而結(jié)束了爭(zhēng)論。《民法通則》的這些規(guī)定,雖然從一定程度上解決了理論上的矛盾,但從另外的角度,又制造了新的矛盾和混亂,使民法學(xué)理論處于潛在的困境之中。
第一,在理論上,引起理論的沖突和認(rèn)識(shí)的混亂,導(dǎo)致民法學(xué)理論整體上的不協(xié)調(diào)。
首先,我國(guó)《民法通則》將民事法律行為界定為合法行為,這一規(guī)定與具體民事法律行為制度理論產(chǎn)生了沖突。例如:合同是一種雙方民事法律行為,而無(wú)效合同也是合同,也應(yīng)是民事法律行為,但無(wú)效合同卻是不合法的法律行為。同樣在婚姻關(guān)系中存在“無(wú)效婚姻”,在繼承關(guān)系中存在“無(wú)效遺囑”等不合法的民事法律行為。本來(lái)法律行為是從合同、遺囑、婚姻等行為中抽象出來(lái)的概念,理應(yīng)反映它們的共同特征和一般本質(zhì),從邏輯學(xué)上講,其外延應(yīng)比合同等下位概念要大,所以僅將民事法律行為界定為合法行為,違反了一般與個(gè)別的辯證關(guān)系。其次,將民事法律行為界定為合法行為,與法理學(xué)關(guān)于法律行為的認(rèn)識(shí)存在嚴(yán)重分歧。法理學(xué)認(rèn)為法律行為是指具有法律意義的行為或能夠產(chǎn)生法律后果的行為,包括合法行為和違法行為[2],并不僅指合法行為。因而,將民事法律行為界定為合法行為,在整個(gè)法學(xué)系統(tǒng)中也存在不協(xié)調(diào)、不一致的問(wèn)題。再次,民事行為的獨(dú)創(chuàng),由于《民法通則》未作明文規(guī)定,使得人們?cè)趯?duì)其含義的理解上莫衷一是:有人認(rèn)為,民事行為是民事法律行為、無(wú)效民事行為和可變更、可撤銷民事行為的屬概念;有人認(rèn)為,民事行為是能夠產(chǎn)生民事法律后果的行為或具有民事法律意義的行為;甚至有人認(rèn)為,民事行為是“統(tǒng)率民法上所有行為的總概念”[3],從而造成對(duì)民事法律事實(shí)理論內(nèi)部結(jié)構(gòu)認(rèn)識(shí)上的混亂。
第二,在立法技術(shù)上,有悖于形式邏輯基本規(guī)則的要求。
首先,通過(guò)對(duì)《民法通則》具體法條的分析,可以知道民事行為包括有效的民事行為、無(wú)效的民事行為和可變更、可撤銷民事行為,其中有效的民事行為就是《民法通則》規(guī)定的民事法律行為,是一個(gè)種概念,而民事行為是一個(gè)屬概念。然而從《民法通則》第四章“民事法律行為和”及其第一節(jié)“民事法律行為”這種立題,以及第一節(jié)“民事法律行為”下作出關(guān)于民事行為的規(guī)定來(lái)看,根據(jù)形式邏輯的概括規(guī)則,“民事法律行為”倒成了屬概念,而“民事行為”反而變成了種概念。其次,從《民法通則》第四章具體條文的表述來(lái)看,有些條文是從民事法律行為的角度出發(fā)來(lái)要求一般民事行為,儼然民事法律行為是民事行為的上位概念。例如,《民法通則》第56條規(guī)定:“民事法律行為可以采取書(shū)面形式、口頭形式或者其他形式”。第62條規(guī)定:“民事法律行為可以附條件,附條件的民事法律行為在符合所附條件時(shí)才生效”。難道只有合法的民事行為才可以“采取書(shū)面形式、口頭形式或其他形式”,才可以“附條件”嗎?
以上兩點(diǎn)實(shí)際上也恰恰反映了立法者內(nèi)心的矛盾心態(tài):一方面引進(jìn)了“民事行為”概念,概括一切合法、不合法的民事法律行為,以解決民事法律行為的“合法卻無(wú)效”的矛盾;另一方面又不舍得放棄民事法律行為的統(tǒng)率性,因?yàn)樗哂泻茇S富的歷史傳統(tǒng)和對(duì)所有意思自治領(lǐng)域民事活動(dòng)強(qiáng)大的示范力量。同時(shí)這也向我們的民法學(xué)研究工作提出了一個(gè)問(wèn)題,即今后對(duì)于民事主體意思表示行為的一般模式研究,是從民事法律行為的角度出發(fā),還是從民事行為的角度出發(fā)?
第三,在立法價(jià)值上,沒(méi)有必要獨(dú)創(chuàng)一個(gè)民事行為。
首先,分析《民法通則》中民事行為和民事法律行為的關(guān)系,我們可以知道,民事法律行為只是一種合法有效的民事行為,那么我們完全可以用合法有效的民事行為作為民事行為的一個(gè)分類概念來(lái)取代民事法律行為。正如人可以分為正常人和病人,卻沒(méi)有必要將正常人用一個(gè)莫名其妙的概念,來(lái)代替“正常人”概念,然而用取消民事法律行為概念的代價(jià)來(lái)解決“合法卻無(wú)效”的矛盾卻也并非我們的本意。
其次,在《民法通則》頒布之前,關(guān)于民事法律行為是否以合法性為要件是存在爭(zhēng)論的,有的學(xué)者早已指出合法性并非民事法律行為的必備要件。如:“法律行為,是權(quán)利主體所從事的,旨在規(guī)定、變更和廢止民事法律關(guān)系的行為。”[4]法律行為,指能夠發(fā)生法律效力的人們的意志行為,即根據(jù)當(dāng)事人的個(gè)人意愿形成的一種有意識(shí)的活動(dòng)……可以分為合法行為和違法行為”[5]。由此可見(jiàn),為了解決“合法卻無(wú)效”的矛盾,學(xué)者們并未僅僅把眼光局限于“法律行為是合法表意行為”上來(lái)考慮獨(dú)創(chuàng)一個(gè)新的概念,而開(kāi)始考慮“合法性”在民事法律行為中的地位了。我國(guó)臺(tái)灣學(xué)者史尚寬先生將民事法律行為的成立和有效區(qū)分為兩個(gè)不同的階段。認(rèn)為合法性只是民事法律行為的有效要件,并非民事法律行為的成立要件[6]。按照這一思路,我們完全可以將民事法律行為劃分為成立和生效兩個(gè)階段,將合法性從民事法律行為的成立要件中剔除,從而解決“合法卻無(wú)效”的矛盾。實(shí)際上,《民法通則》所規(guī)定的民事行為,只不過(guò)是包括合法行為和不合法行為的民事法律行為,即民事法律行為成立狀態(tài)的換種說(shuō)法而已。至此可見(jiàn),我們完全沒(méi)有必要特別地創(chuàng)立“民事行為”這一新概念。而應(yīng)對(duì)民事法律行為概念進(jìn)行重新改造,取消其合法性。
二、取消民事法律行為合法性要件的理論依據(jù)
第一,合法性并非民事法律行為的本質(zhì)特征。
所謂特征乃是一事物區(qū)別于他事
物的標(biāo)志。然而考察民事法律行為與事實(shí)行為的關(guān)系時(shí),可以知道,事實(shí)行為是指行為人主觀上并不具有產(chǎn)生、變更或消滅一定民事法律關(guān)系的意思,只是客觀上由于法律的規(guī)定而產(chǎn)生一定法律后果的行為。事實(shí)行為大多數(shù)情況下是指合法行為,“例如遺失物之拾得、標(biāo)的物之交付等”,它們都屬于民事合法行為,“均能引起民事法律關(guān)系的變化,在當(dāng)事人之間發(fā)生設(shè)立、變更、終止民事權(quán)利和民事義務(wù)的效果”。合法性并不能將民事法律行為同與其相對(duì)應(yīng)的事實(shí)行為區(qū)分開(kāi)。相反,民事法律行為與事實(shí)行為相區(qū)別的根本標(biāo)志在于是否存在意思表示,也即要看法律后果的產(chǎn)生是由當(dāng)事人的主觀意思表示,還是法律的客觀規(guī)定。“可見(jiàn),《民法通則》第54條為民事法律行為所下定義,未能正確揭示民事法律行為的本質(zhì)及其內(nèi)涵和外延。”[7]
第二,合法性并非民事法律行為的必備要件。
任何一項(xiàng)法律制度都要通過(guò)當(dāng)事人的法律行為和國(guó)家的法律評(píng)價(jià)來(lái)落實(shí),這是應(yīng)當(dāng)予以區(qū)別對(duì)待的兩個(gè)不同階段。民事法律行為首先是民事主體的行為,而不是國(guó)家的行為,是民事主體基于自主自愿而為的,以影響一定民事法律關(guān)系為目的的行為,應(yīng)集中體現(xiàn)當(dāng)事人的意思表示,至于該行為本身合法與否,行為產(chǎn)生何種法律效果,是國(guó)家對(duì)其進(jìn)行的法律評(píng)價(jià),不是當(dāng)事人所能隨便確定的。在實(shí)際生活中,當(dāng)事人也往往不可能對(duì)一切意思表示都有正確的法律觀念,意思表示也不可能包括民事法律行為可能發(fā)生的一切法律后果。合法性只是在確定已經(jīng)實(shí)施的民事法律行為的法律后果時(shí)才有意義。所以,合法性是國(guó)家對(duì)民事法律行為的外在評(píng)價(jià)。并不是民事法律行為構(gòu)成的內(nèi)在要求。正如我們不能因?yàn)橐粋€(gè)人是病人而否認(rèn)其為人一樣,也不能因?yàn)橐豁?xiàng)民事法律行為不符合民事法律行為有效要件的要求,而否認(rèn)其為民事法律行為。
第三,意思表示才是民事法律行為的優(yōu)秀要素和本質(zhì)特征。
一方面,意思表示是民事法律行為的優(yōu)秀要素和必備要件,無(wú)意思表示不足以成為民事法律行為,民事法律行為是民事主體旨在設(shè)立、變更或終止一定民事法律關(guān)系的表示行為,集中體現(xiàn)了當(dāng)事人的意思表示。史尚寬先生曾經(jīng)反復(fù)說(shuō)過(guò),“法律行為系以意思表示為要素之法律要件,無(wú)意思表示不得成立法律行為也”,“意思表示以外的事實(shí)雖亦得為法律行為之要件,然不得有不以意思表示為要素之法律行為。”[8]另一方面,意思表示是民事法律行為區(qū)別于其他民事法律事實(shí)的根本特征。無(wú)論是事件中的自然事件、社會(huì)事件,還是行為中的行政行為、司法行為、事實(shí)行為都不具有意思表示。
由此,我們可以圍繞意見(jiàn)表示將民事法律行為界定為:民事主體旨在以設(shè)立、變更、持續(xù)、終止一定民事權(quán)利義務(wù)關(guān)系為目的的表示行為。首先,民事法律行為是行為人以民事主體的身份或資格實(shí)施的行為,并且必須按照民事活動(dòng)的準(zhǔn)則進(jìn)行,以此區(qū)別于行政行為和司法行為,此為民事法體行為構(gòu)成的人的要素;其次,民事法律行為是有目的行為,無(wú)目的行為和精神病患者所為的行為不是民事法律行為,民事法律行為主體行為的目的旨在設(shè)立、變更、持續(xù)或終止一定民事權(quán)利義務(wù)關(guān)系,此為民事法律行為構(gòu)成的目的要素;再次,民事法律行為的優(yōu)秀是意思表示,無(wú)意思表示則不為民事法律行為,以此區(qū)別于事實(shí)行為,此為民事法律行為構(gòu)成的意思表示要素。
三、民事法律行為是一個(gè)發(fā)展的概念,民事法律行為不以合法性為要件符合現(xiàn)代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發(fā)展和人類認(rèn)識(shí)發(fā)展的規(guī)律
所謂概念,“是反映對(duì)象的本質(zhì)屬性的思維形式,人們通過(guò)實(shí)踐從對(duì)象的許多屬性中,撇開(kāi)非本質(zhì)屬性,抽出本質(zhì)屬性概括而成……概念不是永恒不變的,而是隨著社會(huì)歷史和人類認(rèn)識(shí)的發(fā)展而變化的。”[9]由此可見(jiàn),概念是發(fā)展的,而且制約概念發(fā)展的因素有兩個(gè):—是概念所反映的對(duì)象的發(fā)展程度;另一是人們對(duì)于對(duì)象的認(rèn)識(shí)程度。
前文中已說(shuō)明,民事法律行為是商品經(jīng)濟(jì)的產(chǎn)物,是人們應(yīng)商品經(jīng)濟(jì)發(fā)展規(guī)范化、簡(jiǎn)約化的要求,面對(duì)商品生產(chǎn)和商品交換行為的抽象和概括。所以,一方面我們從概念隨所反映的對(duì)象的發(fā)展而發(fā)展的角度來(lái)看,民事法律行為作為商品經(jīng)濟(jì)的產(chǎn)物,也必然要隨著商品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而發(fā)展。考察民事法律行為的原初意義知道其含有合法性,這是因?yàn)楫?dāng)時(shí)商品經(jīng)濟(jì)尚不發(fā)達(dá).商品生產(chǎn)和商品交換行為尚不普遍,國(guó)家對(duì)商品生產(chǎn)和商品交換行為的控制比較嚴(yán)格,因而規(guī)定民事法律行為必須是合法行為,而在現(xiàn)今商品經(jīng)濟(jì)蓬勃發(fā)展的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時(shí)代,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所需要的是具有自覺(jué)性、自主性、自為性、自律性的主體,“經(jīng)濟(jì)和社會(huì)則要求民法給予民事主體以充分的自主權(quán),因此,民事法律行為可以包括不合法的表示行為”[10]。以充分尊重當(dāng)事人的意見(jiàn)表示,這將有利于激發(fā)民事主體的積極性和創(chuàng)造性,尤其是在當(dāng)前社會(huì)主義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體制的建立階段,在私法自治原則漸受肯認(rèn)和尊崇的時(shí)代,強(qiáng)調(diào)意思表示是民事法律行為的優(yōu)秀,就更具有現(xiàn)實(shí)意義了。
另一方面,我們從概念隨著人們對(duì)概念所反映對(duì)象的認(rèn)識(shí)的發(fā)展而發(fā)展的角度來(lái)看,隨著社會(huì)歷史的發(fā)展,人們的認(rèn)識(shí)也應(yīng)該深化。作為科學(xué)研究,理應(yīng)深入探究民事法律行為的本質(zhì)特征。實(shí)際上,民事法律行為中的“法律”是中性詞語(yǔ),只是表明具有法律性而已。所謂法律性主要指民事法律行為是受民法調(diào)整并由民法規(guī)定的行為,是能夠發(fā)生民事法律效果的行為,是民事法律現(xiàn)象的組成部分。民事法律行為的法律性并不表明其必須是合法行為。過(guò)去人們認(rèn)為民事法律行為含有合法性,是囿于當(dāng)時(shí)商品經(jīng)濟(jì)不發(fā)達(dá)的客觀現(xiàn)實(shí),而隨著商品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人們對(duì)反映商品生產(chǎn)和商品交換行為的民事法律行為之本質(zhì)特征的認(rèn)識(shí)自應(yīng)有所深化。
對(duì)于概念的這一發(fā)展過(guò)程,有學(xué)者指出:“概念是從凝固、僵化客觀事物的運(yùn)動(dòng),到突破凝固、僵化,在自身的往返流動(dòng),這就是概念運(yùn)動(dòng)的基本特點(diǎn),……概念所以是運(yùn)動(dòng)的,因?yàn)樗鼈兪橇鬓D(zhuǎn)的變化的客觀事物的反映,這也就是認(rèn)識(shí)運(yùn)動(dòng)的辯證性質(zhì),人類就是在概念的辯證過(guò)程中無(wú)限接近客觀事物本身,在概念和它所反映的現(xiàn)象之間的具體地歷史地統(tǒng)一過(guò)程中認(rèn)識(shí)和改造世界。”[11]對(duì)于民事法律行為不以合法性為要件這一發(fā)展,也是社會(huì)歷史發(fā)展和人類認(rèn)識(shí)發(fā)展相統(tǒng)一的必然結(jié)果。
[摘要] 我國(guó)《民法通則》將民事法律行為界定為合法行為是理論上的一個(gè)失誤,它導(dǎo)致了民法學(xué)理論的沖突和認(rèn)識(shí)的混亂,也違背了邏輯規(guī)則。應(yīng)該對(duì)民事法律行為概念重新認(rèn)識(shí)。合法性并非民事法律行為的本質(zhì)特征、必備要素和成立要件,只能把合法性作為國(guó)家對(duì)當(dāng)事人民事法律行為的法律評(píng)價(jià)和法律控制的生效要件來(lái)對(duì)待。意思表示才是民事法律行為的優(yōu)秀要素和本質(zhì)特征。在現(xiàn)代社會(huì)主義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體制的建立階段,強(qiáng)調(diào)民事法律行為的意思表示要素具有重要的現(xiàn)實(shí)意義,它有利于激發(fā)民事主體的積極性和創(chuàng)造性,符合現(xiàn)代法治的基本精神。而取消民事法律行為的合法性要件是現(xiàn)代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發(fā)展和人類認(rèn)識(shí)發(fā)展相統(tǒng)一的必然結(jié)果。
[關(guān)鍵詞] 民法通則 民事法律行為 合法性 意思表示
民事法律行為制度是民法學(xué)理論的一項(xiàng)基本內(nèi)容,它是聯(lián)結(jié)權(quán)利主體制度、物權(quán)制度、債權(quán)制度這三大民法理論的紐帶;是客觀權(quán)利義務(wù)向主觀權(quán)利義務(wù)跨越的橋梁;是法制度向法現(xiàn)實(shí)轉(zhuǎn)化的接口。民事法律行為是商品經(jīng)濟(jì)的產(chǎn)物,是人們應(yīng)商品經(jīng)濟(jì)發(fā)展規(guī)范化、簡(jiǎn)約化的要求,而對(duì)紛繁復(fù)雜的各種具體的商品生產(chǎn)和商品交換行為進(jìn)行的抽象和概括。可以說(shuō)每一項(xiàng)民法基本精神的實(shí)現(xiàn),社會(huì)主義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新秩序的建立,無(wú)一不依賴于民事法律行為作用的發(fā)揮。所以對(duì)民事法律行為制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shí)踐意義。本文擬從民事法律行為的根本特征人手,來(lái)探討民事法律行為的確切含義。
一、現(xiàn)行民事法律行為制度立法的誤區(qū)
考察民事法律行為概念的歷史沿革,可以知道,民事法律行為原稱為法律行為,起源于德國(guó)法學(xué)家賀古(又譯胡果)所著的《日耳曼普通法》一書(shū)中。法律行為在德語(yǔ)中是Rechtsgesch?ft,由"Recht"和"Gesch?ft"組合而成,其中"Gesch?ft"是“行為”的意思,“Recht”指“法”、“法律”,同時(shí)兼有“公平”、“合法”之意,只是日本學(xué)者借用漢字中的“法律”和“行為”二詞,將“Rechtsgesch?ft”譯為了”法律行為”。[1]因此,法律行為原有意義含有合法性。既為合法表意行為,這在邏輯上顯然存在著矛盾,于是引起了民事法律行為是否以合法性為要件的爭(zhēng)論,學(xué)說(shuō)理論莫衷一是。為了解決這一矛盾,《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民法通則》(以下簡(jiǎn)稱《民法通則》)在立法上,一方面肯定了民事法律行為專指合法行為,一方面特創(chuàng)“民事行為”這一新概念,從而結(jié)束了爭(zhēng)論。《民法通則》的這些規(guī)定,雖然從一定程度上解決了理論上的矛盾,但從另外的角度,又制造了新的矛盾和混亂,使民法學(xué)理論處于潛在的困境之中。
第一,在理論上,引起理論的沖突和認(rèn)識(shí)的混亂,導(dǎo)致民法學(xué)理論整體上的不協(xié)調(diào)。
首先,我國(guó)《民法通則》將民事法律行為界定為合法行為,這一規(guī)定與具體民事法律行為制度理論產(chǎn)生了沖突。例如:合同是一種雙方民事法律行為,而無(wú)效合同也是合同,也應(yīng)是民事法律行為,但無(wú)效合同卻是不合法的法律行為。同樣在婚姻關(guān)系中存在“無(wú)效婚姻”,在繼承關(guān)系中存在“無(wú)效遺囑”等不合法的民事法律行為。本來(lái)法律行為是從合同、遺囑、婚姻等行為中抽象出來(lái)的概念,理應(yīng)反映它們的共同特征和一般本質(zhì),從邏輯學(xué)上講,其外延應(yīng)比合同等下位概念要大,所以僅將民事法律行為界定為合法行為,違反了一般與個(gè)別的辯證關(guān)系。其次,將民事法律行為界定為合法行為,與法理學(xué)關(guān)于法律行為的認(rèn)識(shí)存在嚴(yán)重分歧。法理學(xué)認(rèn)為法律行為是指具有法律意義的行為或能夠產(chǎn)生法律后果的行為,包括合法行為和違法行為[2],并不僅指合法行為。因而,將民事法律行為界定為合法行為,在整個(gè)法學(xué)系統(tǒng)中也存在不協(xié)調(diào)、不一致的問(wèn)題。再次,民事行為的獨(dú)創(chuàng),由于《民法通則》未作明文規(guī)定,使得人們?cè)趯?duì)其含義的理解上莫衷一是:有人認(rèn)為,民事行為是民事法律行為、無(wú)效民事行為和可變更、可撤銷民事行為的屬概念;有人認(rèn)為,民事行為是能夠產(chǎn)生民事法律后果的行為或具有民事法律意義的行為;甚至有人認(rèn)為,民事行為是“統(tǒng)率民法上所有行為的總概念”[3],從而造成對(duì)民事法律事實(shí)理論內(nèi)部結(jié)構(gòu)認(rèn)識(shí)上的混亂。
第二,在立法技術(shù)上,有悖于形式邏輯基本規(guī)則的要求。
首先,通過(guò)對(duì)《民法通則》具體法條的分析,可以知道民事行為包括有效的民事行為、無(wú)效的民事行為和可變更、可撤銷民事行為,其中有效的民事行為就是《民法通則》規(guī)定的民事法律行為,是一個(gè)種概念,而民事行為是一個(gè)屬概念。然而從《民法通則》第四章“民事法律行為和”及其第一節(jié)“民事法律行為”這種立題,以及第一節(jié)“民事法律行為”下作出關(guān)于民事行為的規(guī)定來(lái)看,根據(jù)形式邏輯的概括規(guī)則,“民事法律行為”倒成了屬概念,而“民事行為”反而變成了種概念。其次,從《民法通則》第四章具體條文的表述來(lái)看,有些條文是從民事法律行為的角度出發(fā)來(lái)要求一般民事行為,儼然民事法律行為是民事行為的上位概念。例如,《民法通則》第56條規(guī)定:“民事法律行為可以采取書(shū)面形式、口頭形式或者其他形式”。第62條規(guī)定:“民事法律行為可以附條件,附條件的民事法律行為在符合所附條件時(shí)才生效”。難道只有合法的民事行為才可以“采取書(shū)面形式、口頭形式或其他形式”,才可以“附條件”嗎?
以上兩點(diǎn)實(shí)際上也恰恰反映了立法者內(nèi)心的矛盾心態(tài):一方面引進(jìn)了“民事行為”概念,概括一切合法、不合法的民事法律行為,以解決民事法律行為的“合法卻無(wú)效”的矛盾;另一方面又不舍得放棄民事法律行為的統(tǒng)率性,因?yàn)樗哂泻茇S富的歷史傳統(tǒng)和對(duì)所有意思自治領(lǐng)域民事活動(dòng)強(qiáng)大的示范力量。同時(shí)這也向我們的民法學(xué)研究工作提出了一個(gè)問(wèn)題,即今后對(duì)于民事主體意思表示行為的一般模式研究,是從民事法律行為的角度出發(fā),還是從民事行為的角度出發(fā)?
第三,在立法價(jià)值上,沒(méi)有必要獨(dú)創(chuàng)一個(gè)民事行為。
首先,分析《民法通則》中民事行為和民事法律行為的關(guān)系,我們可以知道,民事法律行為只是一種合法有效的民事行為,那么我們完全可以用合法有效的民事行為作為民事行為的一個(gè)分類概念來(lái)取代民事法律行為。正如人可以分為正常人和病人,卻沒(méi)有必要將正常人用一個(gè)莫名其妙的概念,來(lái)代替“正常人”概念,然而用取消民事法律行為概念的代價(jià)來(lái)解決“合法卻無(wú)效”的矛盾卻也并非我們的本意。
其次,在《民法通則》頒布之前,關(guān)于民事法律行為是否以合法性為要件是存在爭(zhēng)論的,有的學(xué)者早已指出合法性并非民事法律行為的必備要件。如:“法律行為,是權(quán)利主體所從事的,旨在規(guī)定、變更和廢止民事法律關(guān)系的行為。”[4]法律行為,指能夠發(fā)生法律效力的人們的意志行為,即根據(jù)當(dāng)事人的個(gè)人意愿形成的一種有意識(shí)的活動(dòng)……可以分為合法行為和違法行為”[5]。由此可見(jiàn),為了解決“合法卻無(wú)效”的矛盾,學(xué)者們并未僅僅把眼光局限于“法律行為是合法表意行為”上來(lái)考慮獨(dú)創(chuàng)一個(gè)新的概念,而開(kāi)始考慮“合法性”在民事法律行為中的地位了。我國(guó)臺(tái)灣學(xué)者史尚寬先生將民事法律行為的成立和有效區(qū)分為兩個(gè)不同的階段。認(rèn)為合法性只是民事法律行為的有效要件,并非民事法律行為的成立要件[6]。按照這一思路,我們完全可以將民事法律行為劃分為成立和生效兩個(gè)階段,將合法性從民事法律行為的成立要件中剔除,從而解決“合法卻無(wú)效”的矛盾。實(shí)際上,《民法通則》所規(guī)定的民事行為,只不過(guò)是包括合法行為和不合法行為的民事法律行為,即民事法律行為成立狀態(tài)的換種說(shuō)法而已。至此可見(jiàn),我們完全沒(méi)有必要特別地創(chuàng)立“民事行為”這一新概念。而應(yīng)對(duì)民事法律行為概念進(jìn)行重新改造,取消其合法性。
二、取消民事法律行為合法性要件的理論依據(jù)
第一,合法性并非民事法律行為的本質(zhì)特征。
所謂特征乃是一事物區(qū)別于他事物的標(biāo)志。然而考察民事法律行為與事實(shí)行為的關(guān)系時(shí),可以知道,事實(shí)行為是指行為人主觀上并不具有產(chǎn)生、變更或消滅一定民事法律關(guān)系的意思,只是客觀上由于法律的規(guī)定而產(chǎn)生一定法律后果的行為。事實(shí)行為大多數(shù)情況下是指合法行為,“例如遺失物之拾得、標(biāo)的物之交付等”,它們都屬于民事合法行為,“均能引起民事法律關(guān)系的變化,在當(dāng)事人之間發(fā)生設(shè)立、變更、終止民事權(quán)利和民事義務(wù)的效果”。合法性并不能將民事法律行為同與其相對(duì)應(yīng)的事實(shí)行為區(qū)分開(kāi)。相反,民事法律行為與事實(shí)行為相區(qū)別的根本標(biāo)志在于是否存在意思表示,也即要看法律后果的產(chǎn)生是由當(dāng)事人的主觀意思表示,還是法律的客觀規(guī)定。“可見(jiàn),《民法通則》第54條為民事法律行為所下定義,未能正確揭示民事法律行為的本質(zhì)及其內(nèi)涵和外延。”[7]
第二,合法性并非民事法律行為的必備要件。
任何一項(xiàng)法律制度都要通過(guò)當(dāng)事人的法律行為和國(guó)家的法律評(píng)價(jià)來(lái)落實(shí),這是應(yīng)當(dāng)予以區(qū)別對(duì)待的兩個(gè)不同階段。民事法律行為首先是民事主體的行為,而不是國(guó)家的行為,是民事主體基于自主自愿而為的,以影響一定民事法律關(guān)系為目的的行為,應(yīng)集中體現(xiàn)當(dāng)事人的意思表示,至于該行為本身合法與否,行為產(chǎn)生何種法律效果,是國(guó)家對(duì)其進(jìn)行的法律評(píng)價(jià),不是當(dāng)事人所能隨便確定的。在實(shí)際生活中,當(dāng)事人也往往不可能對(duì)一切意思表示都有正確的法律觀念,意思表示也不可能包括民事法律行為可能發(fā)生的一切法律后果。合法性只是在確定已經(jīng)實(shí)施的民事法律行為的法律后果時(shí)才有意義。所以,合法性是國(guó)家對(duì)民事法律行為的外在評(píng)價(jià)。并不是民事法律行為構(gòu)成的內(nèi)在要求。正如我們不能因?yàn)橐粋€(gè)人是病人而否認(rèn)其為人一樣,也不能因?yàn)橐豁?xiàng)民事法律行為不符合民事法律行為有效要件的要求,而否認(rèn)其為民事法律行為。
第三,意思表示才是民事法律行為的優(yōu)秀要素和本質(zhì)特征。
一方面,意思表示是民事法律行為的優(yōu)秀要素和必備要件,無(wú)意思表示不足以成為民事法律行為,民事法律行為是民事主體旨在設(shè)立、變更或終止一定民事法律關(guān)系的表示行為,集中體現(xiàn)了當(dāng)事人的意思表示。史尚寬先生曾經(jīng)反復(fù)說(shuō)過(guò),“法律行為系以意思表示為要素之法律要件,無(wú)意思表示不得成立法律行為也”,“意思表示以外的事實(shí)雖亦得為法律行為之要件,然不得有不以意思表示為要素之法律行為。”[8]另一方面,意思表示是民事法律行為區(qū)別于其他民事法律事實(shí)的根本特征。無(wú)論是事件中的自然事件、社會(huì)事件,還是行為中的行政行為、司法行為、事實(shí)行為都不具有意思表示。
由此,我們可以圍繞意見(jiàn)表示將民事法律行為界定為:民事主體旨在以設(shè)立、變更、持續(xù)、終止一定民事權(quán)利義務(wù)關(guān)系為目的的表示行為。首先,民事法律行為是行為人以民事主體的身份或資格實(shí)施的行為,并且必須按照民事活動(dòng)的準(zhǔn)則進(jìn)行,以此區(qū)別于行政行為和司法行為,此為民事法體行為構(gòu)成的人的要素;其次,民事法律行為是有目的行為,無(wú)目的行為和精神病患者所為的行為不是民事法律行為,民事法律行為主體行為的目的旨在設(shè)立、變更、持續(xù)或終止一定民事權(quán)利義務(wù)關(guān)系,此為民事法律行為構(gòu)成的目的要素;再次,民事法律行為的優(yōu)秀是意思表示,無(wú)意思表示則不為民事法律行為,以此區(qū)別于事實(shí)行為,此為民事法律行為構(gòu)成的意思表示要素。
三、民事法律行為是一個(gè)發(fā)展的概念,民事法律行為不以合法性為要件符合現(xiàn)代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發(fā)展和人類認(rèn)識(shí)發(fā)展的規(guī)律
所謂概念,“是反映對(duì)象的本質(zhì)屬性的思維形式,人們通過(guò)實(shí)踐從對(duì)象的許多屬性中,撇開(kāi)非本質(zhì)屬性,抽出本質(zhì)屬性概括而成……概念不是永恒不變的,而是隨著社會(huì)歷史和人類認(rèn)識(shí)的發(fā)展而變化的。”[9]由此可見(jiàn),概念是發(fā)展的,而且制約概念發(fā)展的因素有兩個(gè):—是概念所反映的對(duì)象的發(fā)展程度;另一是人們對(duì)于對(duì)象的認(rèn)識(shí)程度。
前文中已說(shuō)明,民事法律行為是商品經(jīng)濟(jì)的產(chǎn)物,是人們應(yīng)商品經(jīng)濟(jì)發(fā)展規(guī)范化、簡(jiǎn)約化的要求,面對(duì)商品生產(chǎn)和商品交換行為的抽象和概括。所以,一方面我們從概念隨所反映的對(duì)象的發(fā)展而發(fā)展的角度來(lái)看,民事法律行為作為商品經(jīng)濟(jì)的產(chǎn)物,也必然要隨著商品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而發(fā)展。考察民事法律行為的原初意義知道其含有合法性,這是因?yàn)楫?dāng)時(shí)商品經(jīng)濟(jì)尚不發(fā)達(dá).商品生產(chǎn)和商品交換行為尚不普遍,國(guó)家對(duì)商品生產(chǎn)和商品交換行為的控制比較嚴(yán)格,因而規(guī)定民事法律行為必須是合法行為,而在現(xiàn)今商品經(jīng)濟(jì)蓬勃發(fā)展的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時(shí)代,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所需要的是具有自覺(jué)性、自主性、自為性、自律性的主體,“經(jīng)濟(jì)和社會(huì)則要求民法給予民事主體以充分的自主權(quán),因此,民事法律行為可以包括不合法的表示行為”[10]。以充分尊重當(dāng)事人的意見(jiàn)表示,這將有利于激發(fā)民事主體的積極性和創(chuàng)造性,尤其是在當(dāng)前社會(huì)主義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體制的建立階段,在私法自治原則漸受肯認(rèn)和尊崇的時(shí)代,強(qiáng)調(diào)意思表示是民事法律行為的優(yōu)秀,就更具有現(xiàn)實(shí)意義了。
另一方面,我們從概念隨著人們對(duì)概念所反映對(duì)象的認(rèn)識(shí)的發(fā)展而發(fā)展的角度來(lái)看,隨著社會(huì)歷史的發(fā)展,人們的認(rèn)識(shí)也應(yīng)該深化。作為科學(xué)研究,理應(yīng)深入探究民事法律行為的本質(zhì)特征。實(shí)際上,民事法律行為中的“法律”是中性詞語(yǔ),只是表明具有法律性而已。所謂法律性主要指民事法律行為是受民法調(diào)整并由民法規(guī)定的行為,是能夠發(fā)生民事法律效果的行為,是民事法律現(xiàn)象的組成部分。民事法律行為的法律性并不表明其必須是合法行為。過(guò)去人們認(rèn)為民事法律行為含有合法性,是囿于當(dāng)時(shí)商品經(jīng)濟(jì)不發(fā)達(dá)的客觀現(xiàn)實(shí),而隨著商品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人們對(duì)反映商品生產(chǎn)和商品交換行為的民事法律行為之本質(zhì)特征的認(rèn)識(shí)自應(yīng)有所深化。
對(duì)于概念的這一發(fā)展過(guò)程,有學(xué)者指出:“概念是從凝固、僵化客觀事物的運(yùn)動(dòng),到突破凝固、僵化,在自身的往返流動(dòng),這就是概念運(yùn)動(dòng)的基本特點(diǎn),……概念所以是運(yùn)動(dòng)的,因?yàn)樗鼈兪橇鬓D(zhuǎn)的變化的客觀事物的反映,這也就是認(rèn)識(shí)運(yùn)動(dòng)的辯證性質(zhì),人類就是在概念的辯證過(guò)程中無(wú)限接近客觀事物本身,在概念和它所反映的現(xiàn)象之間的具體地歷史地統(tǒng)一過(guò)程中認(rèn)識(shí)和改造世界。”[11]對(duì)于民事法律行為不以合法性為要件這一發(fā)展,也是社會(huì)歷史發(fā)展和人類認(rèn)識(shí)發(fā)展相統(tǒng)一的必然結(jié)果。
[摘要] 我國(guó)《民法通則》將民事法律行為界定為合法行為是理論上的一個(gè)失誤,它導(dǎo)致了民法學(xué)理論的沖突和認(rèn)識(shí)的混亂,也違背了邏輯規(guī)則。應(yīng)該對(duì)民事法律行為概念重新認(rèn)識(shí)。合法性并非民事法律行為的本質(zhì)特征、必備要素和成立要件,只能把合法性作為國(guó)家對(duì)當(dāng)事人民事法律行為的法律評(píng)價(jià)和法律控制的生效要件來(lái)對(duì)待。意思表示才是民事法律行為的優(yōu)秀要素和本質(zhì)特征。在現(xiàn)代社會(huì)主義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體制的建立階段,強(qiáng)調(diào)民事法律行為的意思表示要素具有重要的現(xiàn)實(shí)意義,它有利于激發(fā)民事主體的積極性和創(chuàng)造性,符合現(xiàn)代法治的基本精神。而取消民事法律行為的合法性要件是現(xiàn)代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發(fā)展和人類認(rèn)識(shí)發(fā)展相統(tǒng)一的必然結(jié)果。
[關(guān)鍵詞] 民法通則 民事法律行為 合法性 意思表示
民事法律行為制度是民法學(xué)理論的一項(xiàng)基本內(nèi)容,它是聯(lián)結(jié)權(quán)利主體制度、物權(quán)制度、債權(quán)制度這三大民法理論的紐帶;是客觀權(quán)利義務(wù)向主觀權(quán)利義務(wù)跨越的橋梁;是法制度向法現(xiàn)實(shí)轉(zhuǎn)化的接口。民事法律行為是商品經(jīng)濟(jì)的產(chǎn)物,是人們應(yīng)商品經(jīng)濟(jì)發(fā)展規(guī)范化、簡(jiǎn)約化的要求,而對(duì)紛繁復(fù)雜的各種具體的商品生產(chǎn)和商品交換行為進(jìn)行的抽象和概括。可以說(shuō)每一項(xiàng)民法基本精神的實(shí)現(xiàn),社會(huì)主義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新秩序的建立,無(wú)一不依賴于民事法律行為作用的發(fā)揮。所以對(duì)民事法律行為制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shí)踐意義。本文擬從民事法律行為的根本特征人手,來(lái)探討民事法律行為的確切含義。
一、現(xiàn)行民事法律行為制度立法的誤區(qū)
考察民事法律行為概念的歷史沿革,可以知道,民事法律行為原稱為法律行為,起源于德國(guó)法學(xué)家賀古(又譯胡果)所著的《日耳曼普通法》一書(shū)中。法律行為在德語(yǔ)中是Rechtsgesch?ft,由"Recht"和"Gesch?ft"組合而成,其中"Gesch?ft"是“行為”的意思,“Recht”指“法”、“法律”,同時(shí)兼有“公平”、“合法”之意,只是日本學(xué)者借用漢字中的“法律”和“行為”二詞,將“Rechtsgesch?ft”譯為了”法律行為”。[1]因此,法律行為原有意義含有合法性。既為合法表意行為,這在邏輯上顯然存在著矛盾,于是引起了民事法律行為是否以合法性為要件的爭(zhēng)論,學(xué)說(shuō)理論莫衷一是。為了解決這一矛盾,《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民法通則》(以下簡(jiǎn)稱《民法通則》)在立法上,一方面肯定了民事法律行為專指合法行為,一方面特創(chuàng)“民事行為”這一新概念,從而結(jié)束了爭(zhēng)論。《民法通則》的這些規(guī)定,雖然從一定程度上解決了理論上的矛盾,但從另外的角度,又制造了新的矛盾和混亂,使民法學(xué)理論處于潛在的困境之中。
第一,在理論上,引起理論的沖突和認(rèn)識(shí)的混亂,導(dǎo)致民法學(xué)理論整體上的不協(xié)調(diào)。
首先,我國(guó)《民法通則》將民事法律行為界定為合法行為,這一規(guī)定與具體民事法律行為制度理論產(chǎn)生了沖突。例如:合同是一種雙方民事法律行為,而無(wú)效合同也是合同,也應(yīng)是民事法律行為,但無(wú)效合同卻是不合法的法律行為。同樣在婚姻關(guān)系中存在“無(wú)效婚姻”,在繼承關(guān)系中存在“無(wú)效遺囑”等不合法的民事法律行為。本來(lái)法律行為是從合同、遺囑、婚姻等行為中抽象出來(lái)的概念,理應(yīng)反映它們的共同特征和一般本質(zhì),從邏輯學(xué)上講,其外延應(yīng)比合同等下位概念要大,所以僅將民事法律行為界定為合法行為,違反了一般與個(gè)別的辯證關(guān)系。其次,將民事法律行為界定為合法行為,與法理學(xué)關(guān)于法律行為的認(rèn)識(shí)存在嚴(yán)重分歧。法理學(xué)認(rèn)為法律行為是指具有法律意義的行為或能夠產(chǎn)生法律后果的行為,包括合法行為和違法行為[2],并不僅指合法行為。因而,將民事法律行為界定為合法行為,在整個(gè)法學(xué)系統(tǒng)中也存在不協(xié)調(diào)、不一致的問(wèn)題。再次,民事行為的獨(dú)創(chuàng),由于《民法通則》未作明文規(guī)定,使得人們?cè)趯?duì)其含義的理解上莫衷一是:有人認(rèn)為,民事行為是民事法律行為、無(wú)效民事行為和可變更、可撤銷民事行為的屬概念;有人認(rèn)為,民事行為是能夠產(chǎn)生民事法律后果的行為或具有民事法律意義的行為;甚至有人認(rèn)為,民事行為是“統(tǒng)率民法上所有行為的總概念”[3],從而造成對(duì)民事法律事實(shí)理論內(nèi)部結(jié)構(gòu)認(rèn)識(shí)上的混亂。
第二,在立法技術(shù)上,有悖于形式邏輯基本規(guī)則的要求。
首先,通過(guò)對(duì)《民法通則》具體法條的分析,可以知道民事行為包括有效的民事行為、無(wú)效的民事行為和可變更、可撤銷民事行為,其中有效的民事行為就是《民法通則》規(guī)定的民事法律行為,是一個(gè)種概念,而民事行為是一個(gè)屬概念。然而從《民法通則》第四章“民事法律行為和”及其第一節(jié)“民事法律行為”這種立題,以及第一節(jié)“民事法律行為”下作出關(guān)于民事行為的規(guī)定來(lái)看,根據(jù)形式邏輯的概括規(guī)則,“民事法律行為”倒成了屬概念,而“民事行為”反而變成了種概念。其次,從《民法通則》第四章具體條文的表述來(lái)看,有些條文是從民事法律行為的角度出發(fā)來(lái)要求一般民事行為,儼然民事法律行為是民事行為的上位概念。例如,《民法通則》第56條規(guī)定:“民事法律行為可以采取書(shū)面形式、口頭形式或者其他形式”。第62條規(guī)定:“民事法律行為可以附條件,附條件的民事法律行為在符合所附條件時(shí)才生效”。難道只有合法的民事行為才可以“采取書(shū)面形式、口頭形式或其他形式”,才可以“附條件”嗎?
以上兩點(diǎn)實(shí)際上也恰恰反映了立法者內(nèi)心的矛盾心態(tài):一方面引進(jìn)了“民事行為”概念,概括一切合法、不合法的民事法律行為,以解決民事法律行為的“合法卻無(wú)效”的矛盾;另一方面又不舍得放棄民事法律行為的統(tǒng)率性,因?yàn)樗哂泻茇S富的歷史傳統(tǒng)和對(duì)所有意思自治領(lǐng)域民事活動(dòng)強(qiáng)大的示范力量。同時(shí)這也向我們的民法學(xué)研究工作提出了一個(gè)問(wèn)題,即今后對(duì)于民事主體意思表示行為的一般模式研究,是從民事法律行為的角度出發(fā),還是從民事行為的角度出發(fā)?
第三,在立法價(jià)值上,沒(méi)有必要獨(dú)創(chuàng)一個(gè)民事行為。
首先,分析《民法通則》中民事行為和民事法律行為的關(guān)系,我們可以知道,民事法律行為只是一種合法有效的民事行為,那么我們完全可以用合法有效的民事行為作為民事行為的一個(gè)分類概念來(lái)取代民事法律行為。正如人可以分為正常人和病人,卻沒(méi)有必要將正常人用一個(gè)莫名其妙的概念,來(lái)代替“正常人”概念,然而用取消民事法律行為概念的代價(jià)來(lái)解決“合法卻無(wú)效”的矛盾卻也并非我們的本意。
其次,在《民法通則》頒布之前,關(guān)于民事法律行為是否以合法性為要件是存在爭(zhēng)論的,有的學(xué)者早已指出合法性并非民事法律行為的必備要件。如:“法律行為,是權(quán)利主體所從事的,旨在規(guī)定、變更和廢止民事法律關(guān)系的行為。”[4]法律行為,指能夠發(fā)生法律效力的人們的意志行為,即根據(jù)當(dāng)事人的個(gè)人意愿形成的一種有意識(shí)的活動(dòng)……可以分為合法行為和違法行為”[5]。由此可見(jiàn),為了解決“合法卻無(wú)效”的矛盾,學(xué)者們并未僅僅把眼光局限于“法律行為是合法表意行為”上來(lái)考慮獨(dú)創(chuàng)一個(gè)新的概念,而開(kāi)始考慮“合法性”在民事法律行為中的地位了。我國(guó)臺(tái)灣學(xué)者史尚寬先生將民事法律行為的成立和有效區(qū)分為兩個(gè)不同的階段。認(rèn)為合法性只是民事法律行為的有效要件,并非民事法律行為的成立要件[6]。按照這一思路,我們完全可以將民事法律行為劃分為成立和生效兩個(gè)階段,將合法性從民事法律行為的成立要件中剔除,從而解決“合法卻無(wú)效”的矛盾。實(shí)際上,《民法通則》所規(guī)定的民事行為,只不過(guò)是包括合法行為和不合法行為的民事法律行為,即民事法律行為成立狀態(tài)的換種說(shuō)法而已。至此可見(jiàn),我們完全沒(méi)有必要特別地創(chuàng)立“民事行為”這一新概念。而應(yīng)對(duì)民事法律行為概念進(jìn)行重新改造,取消其合法性。
二、取消民事法律行為合法性要件的理論依據(jù)
第一,合法性并非民事法律行為的本質(zhì)特征。
所謂特征乃是一事物區(qū)別于他事物的標(biāo)志。然而考察民事法律行為與事實(shí)行為的關(guān)系時(shí),可以知道,事實(shí)行為是指行為人主觀上并不具有產(chǎn)生、變更或消滅一定民事法律關(guān)系的意思,只是客觀上由于法律的規(guī)定而產(chǎn)生一定法律后果的行為。事實(shí)行為大多數(shù)情況下是指合法行為,“例如遺失物之拾得、標(biāo)的物之交付等”,它們都屬于民事合法行為,“均能引起民事法律關(guān)系的變化,在當(dāng)事人之間發(fā)生設(shè)立、變更、終止民事權(quán)利和民事義務(wù)的效果”。合法性并不能將民事法律行為同與其相對(duì)應(yīng)的事實(shí)行為區(qū)分開(kāi)。相反,民事法律行為與事實(shí)行為相區(qū)別的根本標(biāo)志在于是否存在意思表示,也即要看法律后果的產(chǎn)生是由當(dāng)事人的主觀意思表示,還是法律的客觀規(guī)定。“可見(jiàn),《民法通則》第54條為民事法律行為所下定義,未能正確揭示民事法律行為的本質(zhì)及其內(nèi)涵和外延。”[7]
第二,合法性并非民事法律行為的必備要件。
任何一項(xiàng)法律制度都要通過(guò)當(dāng)事人的法律行為和國(guó)家的法律評(píng)價(jià)來(lái)落實(shí),這是應(yīng)當(dāng)予以區(qū)別對(duì)待的兩個(gè)不同階段。民事法律行為首先是民事主體的行為,而不是國(guó)家的行為,是民事主體基于自主自愿而為的,以影響一定民事法律關(guān)系為目的的行為,應(yīng)集中體現(xiàn)當(dāng)事人的意思表示,至于該行為本身合法與否,行為產(chǎn)生何種法律效果,是國(guó)家對(duì)其進(jìn)行的法律評(píng)價(jià),不是當(dāng)事人所能隨便確定的。在實(shí)際生活中,當(dāng)事人也往往不可能對(duì)一切意思表示都有正確的法律觀念,意思表示也不可能包括民事法律行為可能發(fā)生的一切法律后果。合法性只是在確定已經(jīng)實(shí)施的民事法律行為的法律后果時(shí)才有意義。所以,合法性是國(guó)家對(duì)民事法律行為的外在評(píng)價(jià)。并不是民事法律行為構(gòu)成的內(nèi)在要求。正如我們不能因?yàn)橐粋€(gè)人是病人而否認(rèn)其為人一樣,也不能因?yàn)橐豁?xiàng)民事法律行為不符合民事法律行為有效要件的要求,而否認(rèn)其為民事法律行為。
第三,意思表示才是民事法律行為的優(yōu)秀要素和本質(zhì)特征。
一方面,意思表示是民事法律行為的優(yōu)秀要素和必備要件,無(wú)意思表示不足以成為民事法律行為,民事法律行為是民事主體旨在設(shè)立、變更或終止一定民事法律關(guān)系的表示行為,集中體現(xiàn)了當(dāng)事人的意思表示。史尚寬先生曾經(jīng)反復(fù)說(shuō)過(guò),“法律行為系以意思表示為要素之法律要件,無(wú)意思表示不得成立法律行為也”,“意思表示以外的事實(shí)雖亦得為法律行為之要件,然不得有不以意思表示為要素之法律行為。”[8]另一方面,意思表示是民事法律行為區(qū)別于其他民事法律事實(shí)的根本特征。無(wú)論是事件中的自然事件、社會(huì)事件,還是行為中的行政行為、司法行為、事實(shí)行為都不具有意思表示。
由此,我們可以圍繞意見(jiàn)表示將民事法律行為界定為:民事主體旨在以設(shè)立、變更、持續(xù)、終止一定民事權(quán)利義務(wù)關(guān)系為目的的表示行為。首先,民事法律行為是行為人以民事主體的身份或資格實(shí)施的行為,并且必須按照民事活動(dòng)的準(zhǔn)則進(jìn)行,以此區(qū)別于行政行為和司法行為,此為民事法體行為構(gòu)成的人的要素;其次,民事法律行為是有目的行為,無(wú)目的行為和精神病患者所為的行為不是民事法律行為,民事法律行為主體行為的目的旨在設(shè)立、變更、持續(xù)或終止一定民事權(quán)利義務(wù)關(guān)系,此為民事法律行為構(gòu)成的目的要素;再次,民事法律行為的優(yōu)秀是意思表示,無(wú)意思表示則不為民事法律行為,以此區(qū)別于事實(shí)行為,此為民事法律行為構(gòu)成的意思表示要素。
三、民事法律行為是一個(gè)發(fā)展的概念,民事法律行為不以合法性為要件符合現(xiàn)代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發(fā)展和人類認(rèn)識(shí)發(fā)展的規(guī)律
所謂概念,“是反映對(duì)象的本質(zhì)屬性的思維形式,人們通過(guò)實(shí)踐從對(duì)象的許多屬性中,撇開(kāi)非本質(zhì)屬性,抽出本質(zhì)屬性概括而成……概念不是永恒不變的,而是隨著社會(huì)歷史和人類認(rèn)識(shí)的發(fā)展而變化的。”[9]由此可見(jiàn),概念是發(fā)展的,而且制約概念發(fā)展的因素有兩個(gè):—是概念所反映的對(duì)象的發(fā)展程度;另一是人們對(duì)于對(duì)象的認(rèn)識(shí)程度。
前文中已說(shuō)明,民事法律行為是商品經(jīng)濟(jì)的產(chǎn)物,是人們應(yīng)商品經(jīng)濟(jì)發(fā)展規(guī)范化、簡(jiǎn)約化的要求,面對(duì)商品生產(chǎn)和商品交換行為的抽象和概括。所以,一方面我們從概念隨所反映的對(duì)象的發(fā)展而發(fā)展的角度來(lái)看,民事法律行為作為商品經(jīng)濟(jì)的產(chǎn)物,也必然要隨著商品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而發(fā)展。考察民事法律行為的原初意義知道其含有合法性,這是因?yàn)楫?dāng)時(shí)商品經(jīng)濟(jì)尚不發(fā)達(dá).商品生產(chǎn)和商品交換行為尚不普遍,國(guó)家對(duì)商品生產(chǎn)和商品交換行為的控制比較嚴(yán)格,因而規(guī)定民事法律行為必須是合法行為,而在現(xiàn)今商品經(jīng)濟(jì)蓬勃發(fā)展的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時(shí)代,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所需要的是具有自覺(jué)性、自主性、自為性、自律性的主體,“經(jīng)濟(jì)和社會(huì)則要求民法給予民事主體以充分的自主權(quán),因此,民事法律行為可以包括不合法的表示行為”[10]。以充分尊重當(dāng)事人的意見(jiàn)表示,這將有利于激發(fā)民事主體的積極性和創(chuàng)造性,尤其是在當(dāng)前社會(huì)主義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體制的建立階段,在私法自治原則漸受肯認(rèn)和尊崇的時(shí)代,強(qiáng)調(diào)意思表示是民事法律行為的優(yōu)秀,就更具有現(xiàn)實(shí)意義了。
另一方面,我們從概念隨著人們對(duì)概念所反映對(duì)象的認(rèn)識(shí)的發(fā)展而發(fā)展的角度來(lái)看,隨著社會(huì)歷史的發(fā)展,人們的認(rèn)識(shí)也應(yīng)該深化。作為科學(xué)研究,理應(yīng)深入探究民事法律行為的本質(zhì)特征。實(shí)際上,民事法律行為中的“法律”是中性詞語(yǔ),只是表明具有法律性而已。所謂法律性主要指民事法律行為是受民法調(diào)整并由民法規(guī)定的行為,是能夠發(fā)生民事法律效果的行為,是民事法律現(xiàn)象的組成部分。民事法律行為的法律性并不表明其必須是合法行為。過(guò)去人們認(rèn)為民事法律行為含有合法性,是囿于當(dāng)時(shí)商品經(jīng)濟(jì)不發(fā)達(dá)的客觀現(xiàn)實(shí),而隨著商品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人們對(duì)反映商品生產(chǎn)和商品交換行為的民事法律行為之本質(zhì)特征的認(rèn)識(shí)自應(yīng)有所深化。
對(duì)于概念的這一發(fā)展過(guò)程,有學(xué)者指出:“概念是從凝固、僵化客觀事物的運(yùn)動(dòng),到突破凝固、僵化,在自身的往返流動(dòng),這就是概念運(yùn)動(dòng)的基本特點(diǎn),……概念所以是運(yùn)動(dòng)的,因?yàn)樗鼈兪橇鬓D(zhuǎn)的變化的客觀事物的反映,這也就是認(rèn)識(shí)運(yùn)動(dòng)的辯證性質(zhì),人類就是在概念的辯證過(guò)程中無(wú)限接近客觀事物本身,在概念和它所反映的現(xiàn)象之間的具體地歷史地統(tǒng)一過(guò)程中認(rèn)識(shí)和改造世界。”[11]對(duì)于民事法律行為不以合法性為要件這一發(fā)展,也是社會(huì)歷史發(fā)展和人類認(rèn)識(shí)發(fā)展相統(tǒng)一的必然結(jié)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