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07-14 18:28:59
開篇:寫作不僅是一種記錄,更是一種創造,它讓我們能夠捕捉那些稍縱即逝的靈感,將它們永久地定格在紙上。下面是小編精心整理的12篇數學知識論文,希望這些內容能成為您創作過程中的良師益友,陪伴您不斷探索和進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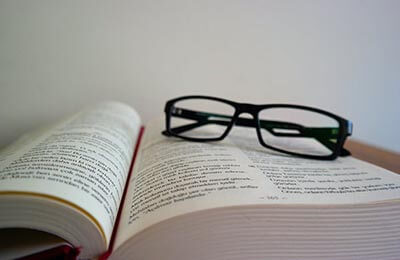
1988年,P.麥蒂(PenelopeMaddy)在《符號邏輯雜志》上發表了兩篇綜述性論文《相信公理I》和《相信公理II》。這兩篇文章的主要貢獻是概括和總結了支持集合論公理,尤其是那些候選新公理的各種證據。在《相信公理I》中闡述ZFC公理的合理依據時,麥蒂引用了G.H.摩爾(GregoryH.Moore)、M.哈雷特(MichaelHallett)以及A.A.弗蘭克爾(AbrahamA.Fraenkel)和A.利維(AzrielLevy)、王浩、F.R.德瑞克(FrankR.Drake)等人的著作和論文。相比于為ZFC公理提供辯護來說,她更強調,它們與未經證實的新公理相比不具有優先的認識論或形而上學地位。麥蒂還考察了人們對CH的態度。她除了參考上述學者的著述外,還引述了數學家、邏輯學家和集合論專家如科恩、哥德爾、D.司克脫(DanaScott)、D.A.馬丁(DonaldA.Martin)、R.M.索羅維(RobertM.Solovay)、C.弗賴林(ChrisFreiling)等人的論文。從她的綜述看到,盡管獨立性命題使得一些人,如科恩一開始采取形式主義的態度,但最終人們對CH具有確定的真值取得一致的意見,即集宇宙的存在支持CH是個真問題,所以引進新公理是必要的。另外,盡管CH的真值尚未判定,但多數人基于各種理由,傾向于猜測它為假。隨著尋找新公理解決連續統問題工作的展開,最普遍被接受的新公理的內在理由是反射原則(reflectionprinciple)。它的基本思想是,集宇宙如此復雜以致不可能被完全描述,因此關于整個集宇宙的任何真,必定已經在該宇宙的某初始段為真。這樣,哥德爾用迭代概念辯護的不可達基數和馬羅基數、甚至比它們更強的弱緊致基數、不可描述基數等都可以在反射原則下得到辯護,而且ZFC公理也可以重塑為反射原則。最終的結果顯示,這些無窮公理都不能判定連續統問題的假,因為它們與證明連續統假設與ZFC公理相容的可構造公理V=L也相容。至于新公理的外在證成方面,人們一般都接受哥德爾聲稱的推論上的富有成果性。麥蒂在《相信公理II》中詳細闡述那些不能用內在理由辯護的大基數公理的推論,尤其是二階數論上的推論。她的論述顯示,現代集合論研究中斷定可測基數、武丁基數和超緊致基數等存在的更大的大基數公理以及涉及可定義實數的決定性公理都具有各自豐富的推論,因此得到了外在的辯護。這些技術工作主要歸功于索羅維、馬丁、M.福爾曼(MatthewForeman)、M.穆加多爾(MenachemMagidor)、S.謝拉(SaharonShelah)、W.H.武丁(WilliamHughWoodin)等人。值得談及的是,60年代后期,索羅維猜想大基數公理蘊涵可定義實數的決定性公理;80年代中期,武丁作為索羅維的學生,最終證明了可定義實數的決定性公理等價于大基數公理的內模型。這個結果產生的影響是,使得兩類在概念上處于完全不同領域的公理被統一起來:決定性公理繼承了大基數公理的內在和外在證據,大基數公理轉而獲得支持決定性公理的外在理由。但與人們期望的相反,這些大基數公理依然無法解決連續統假設問題,盡管它們與V=L不相容。麥蒂撰寫這兩篇綜述性的論文,旨在給數學知識論者和數學哲學家提出哲學任務。她本人認為集合論在可應用性上的成功以及那些外在證據可以鞏固公理的辯護實踐。但她不傾向在某特定的哲學立場上給出新公理的辯護和反駁,而是認為對任何哲學立場的人來說,連續統假設都是一個真問題。因此,在她看來,尋找新公理解決連續統問題不只是柏拉圖主義的事業,而且是對任何哲學立場都重要的事業,關鍵在于深入考察這些哲學立場之間的細小差異。
新公理綱領分歧的當代視野
20世紀90年代后,與麥蒂觀點的初衷事與愿違的是,一些人對連續統具有確定的真值提出了質疑,他們認為獨立性的結果破壞了集合論作為客觀的事業;而包括麥蒂在內的另一些人則堅持獨立性的結果僅僅表明,缺少用于證明這些數學陳述的集合論公理。這種分歧往往伴隨著形而上學立場的分歧,如1999年S.費弗曼(SolomonFeferman)發表于《美國數學月刊》上的論文《數學需要新公理嗎?》以及2000年《符號邏輯簡報》(TheBulletinofSymbolicLogic)上收錄的費弗曼、麥蒂、J.R.斯蒂爾(JohnRobertSteel)等人在2000年符號邏輯年會上的會議論文均體現出這種分歧。爭論的焦點主要表現為如下幾個方面:(一)公理意指什么費弗曼在兩篇文章的開頭均引用了《牛津英語字典》的定義,說明他的“公理”含義即自明性。然后,他把公理的自明性歸因于數學概念的清晰直觀。依照這個標準,他認為皮亞諾算術公理符合這個自明性的標準,因為自然數概念是清晰直觀的。但斯蒂爾認為公理的自明性標準太主觀了,不僅導致無法解決“何謂自明的”爭論,而且產生的公理系統相當有限。他主張,迫使我們接受公理為真的更可能是作為整體的公理系統,而且這個過程是漸進的。因此,盡管我們對新公理的信心不可能達到對皮亞諾公理的信心,但引進的新公理可以合理地得到辯護。麥蒂則分析了費弗曼青睞自明性公理,對外在辯護的新公理無動于衷的原因。她認為,主要原因是,費弗曼要求被辯護的公理不僅表明理論是有效的,還必須符合某種數學概念。這種數學概念是“某理想世界中的概念,……或多或少直接表達想象的事物”④,因此,在麥蒂看來,費弗曼為公理的辯護實際上最終不是基于自明性,而是某種客觀實在。麥蒂自己則更愿意支持外在辯護的新公理,因為它們有助于當代集合論滿足各種目標。但她不認為集合論應當揭示數學實體是什么,或在是否需要新公理的問題上提供認識論基礎,也不認為集合論顯示如何通過顯然的步驟,從絕對的某些真理推導出各種數學真理。(二)連續統假設是否是一個真正的問題費弗曼聲稱連續統假設本質上是模糊的,沒有新公理以令人信服的明確方式解決它。原因在于,連續統(或自然數的冪集)是經由自然數的“任意子集”匯集成一個總體得到的概念;解決連續統問題還需要三階數論上的語句,即需要涉及連續統(實數)的任意子集以及它們之間的可能映射。但“自然數的任意子集”的概念和“實數的任意子集”的概念都是含糊的,因為我們缺少對這些概念的集合直觀,“沒法用合理的方式表明在不違反這個概念應該是什么的情況下形成這個概念。”⑤因此談論CH的真假沒有意義。另外,CH沒有成為千禧年獎金列出的杰出數學問題之一,所以不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但是,斯蒂爾認為三階數論僅僅是語言上的含糊性,這并不代表它本質上就是含糊的。事實上,可以通過提高語言的意義來發現新的真理。最終,解決連續統問題可能就是解決語言上的含糊性。并且一旦澄清了CH在語言中的含糊性,CH在思想中的真就能顯現出來。另外,連續統假設沒有成為七個杰出問題之一,僅僅說明人們對數學基礎問題不感興趣。真正的關鍵是,連續統假設涉及“與數學證據有關的基本概念問題”,值得邏輯學家去關注。麥蒂則擺脫了這樣的問題。原因在于她的自然主義哲學不需要關心CH是否是本質上含糊的,而且她不認為CH的答案是預先確定的。麥蒂的自然主義哲學只需要評估尋找新公理的前景,它符合集合論的目標,也可以解決CH。(三)新公理的辯護依賴于柏拉圖主義的立場是否恰當費弗曼對于用柏拉圖主義為當代集合論尋找新公理提供基本辯護表現出極端的不滿。根據他的理解,柏拉圖主義為當代集合論實踐作辯護主要體現在:CH具有確定的真值訴諸于某個柏拉圖的集合世界;集合的累積分層使用了“給定集合的任意子集”的柏拉圖主義概念。但是,在費弗曼看來,明顯的事實是,不僅CH是含糊的,而且整個累積分層的概念都是內在含糊的。因此不僅談論三階數論上CH的真假沒有意義,而且談論二階數論上陳述的真或假的事實也沒有意義。這種觀點,不僅使得費弗曼只在工具主義的立場承認ZFC從累積分層中產生,而且否認尋找新公理解決這些概念上含糊的獨立性陳述。但麥蒂指出,費弗曼錯誤地相信只有柏拉圖主義能夠為集合論的實踐提供辯護,從而誤以為尋找集合論新公理的實踐是不正當的。她聲稱,哲學不應該證成或批評集合論實踐,它們只是“嘗試理解該實踐”⑥。(四)普通數學是否需要新公理費弗曼認為,沒有證據表明需要新公理解決開放的算術和有窮組合問題。一方面,普通數學不需要新公理。就純數學來說,幾乎所有經典數學的陳述都可以在ZFC中形式化。就應用數學來說,它們都可以在可還原到PA的系統中形式化或者在相對較弱的非直謂分析子系統中實現。因此,他聲稱,由哥德爾第一不完全性定理導致的獨立性命題,應該僅僅是普通數學推理的結果。另一方面,他認為,說需要新公理[即大基數公理(簡稱LCA)]解決不可判定的命題,其實是在回避問題。因為我們尋找的不是新公理,而是它與ZFC的一致性。但在接受ZFC+LCA和接受Con(ZFC+LCA)(“Con”表示“一致或相容”)之間存在差別。在不承認大基數公理具有確定真值的情況下,如果有理由接受Con(ZFC+LCA)但不接受ZFC+LCA,那么我們不應當視LCA為公理。在承認大基數公理有真值的情況下,可以忽略Con(ZFC+LCA)和ZFC+LCA之間的差別,但是還需要說明為什么承認LCA而不是它的否定為真。這兩種情況都說明,我們不應該如同接受皮亞諾算術公理一樣接受它們。麥蒂針對費弗曼提出的第一個理由給出了反駁。她認為ZFC甚至更弱的系統對于當代科學可能夠用,但或許實踐科學并非根據這些較弱系統就能得到,而且純數學的本質就在于自由。因此本著探索的精神,使用非直謂方法和更高的無窮公理是必要的,從而期望獲得更多數學上有趣的結構。斯蒂爾針對費弗曼的第二個理由提出質疑。他認為,費弗曼僅僅說尋找新公理對多數數學家來說不重要,但沒有說明ZFC+LCA和Con(ZFC+LCA)之間不同的實際行為內容可能是什么,也沒有回答解決第二類獨立性命題的大基數公理是否應當算作好的證據,或者是否應該尋找其他方向的解決方案。從上述的爭辯可以看出,費弗曼、麥蒂和斯蒂爾的分歧最終落在經由外在辯護的新公理是否合法的問題上。這種分歧的根源在于,費弗曼基于自然數的實在論立場支持一階數論公理,否認尋找二階以上的數論公理;麥蒂認為尋找新公理不涉及哲學立場的考慮,只需要根植于集合論的實踐目標。斯蒂爾和麥蒂的觀點大體一致,只是他在闡述怎樣算是連續統問題的解決時,還強調哲學在新公理綱領中可以扮演更積極的角色。
新公理討論的最新進展
2000年后,贊同尋找新公理的諸多學者希望為新公理綱領提供更好的辯護,而費弗曼等則依然堅持己見,認為連續統假設是含糊的問題。(一)柏拉圖主義立場的辯護美國數學家和集合論專家武丁自80年代開始,努力尋求連續統問題的解決。他在2004年的論文《羅素之后的集合論:回到伊甸園》中攻擊反柏拉圖主義者關于集合論意義的不可知論,認為連
摘要:科學知識社會學自上世紀7O年代中期產生以來,一直致力于對科學的知識進行懷疑和批判,試圖說明科學知識的形成過程、科學認識的成果無不包含著社會的內容。愛丁堡學派的“強綱領”和“利益模式”為我們認識科學知識的客觀性提供了有益的借鑒。
一、科學知識社會學產生的背景
自從“正統的”科學哲學提出的科學的客觀性以來,對科學的客觀性懷疑,不僅不斷地來自科學哲學內部,以至發展到先是歷史主義學派對客觀性的弱化,再到后現代思潮者那里時,科學的客觀性已無任何立錐之地。除此以外,還有來自哲學以外的解構形式和途徑,而這些當中要首推科學知識社會學對客觀性的解構最為有力、徹底。
以默頓科學社會學為直接的理論來源,以知識社會學理論為間接的知識來源,在經過社會學和哲學對曼海姆知識社會學所留下的問題(主要是兩類知識的劃分是否合理,劃界的標準是否成立,科學知識該不該享有特權和科學知識該不該免于社會學研究)的探討以及反思科學社會學幾十年的發展歷程而出現了科學知識社會學。論文百事通這是由于發生在歐洲的這場科學社會學的研究注重的是科學的“實質性理論”(即科學知識過程)的研究,故一般人常稱其為科學知識社會學,又由于那些研究學者們的工作大多從庫恩思想中獲得過重要啟迪,故也有人把這些工作籠統叫作“后庫恩科學社會學”。科學知識社會學產生于20世紀70年代中期,在20世紀70年代末獲得迅速發展。這一思想來源于維特根斯坦和哈貝馬斯的懷疑主義批判精神,這種懷疑主義批判精神對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產生起著導向作用,晚年的維特根斯坦開始對自然科學知識享有免于社會學研究的特權提出異議,認為科學也有其限度,也應該被視為一種文化現象,并進一步提出知識就其本性而言是社會的。按此線索,維特根斯坦為科學知識的社會學研究奠定了認識論基礎,他明確表示了對科學知識普遍一致性的懷疑,這種態度直接危及兩類知識的劃界標準。哈貝馬斯的批評試圖確立這樣的事實,自然科學的知識是知識體系中的一種形態而已,它的存在是為滿足人類某方面利益的需要,人們在發展這種知識時不可能不滲透利益因素,哈貝馬斯的意圖在于:他想借助于對科學知識的利益解釋來否定科學知識生產過程中的情感中立假設,而這對于奉行培根主義的“科學始于觀察,經驗事實是建立在客觀觀察基礎之上,科學理論又是建立在經驗事實基礎之上”的歸納方法來說是致命一擊,此外哈貝馬斯還強調解釋學和批判的重要性,認為認知主體是有目的的作用于客體,人類的利益動機才是維系科學活動的根本動力。
科學知識社會學的全部工作中心就在于說明科學的認識因素與社會因素的結合,在于說明科學知識的形成過程、科學認識的成果無不包含著社會的內容,最終得到其提出的科學知識是非描述性的,而是社會建構的主旨。真正實踐并致力于科學知識社會學研究的是英國的愛丁堡學派。
二、愛丁堡學派的“強綱領”
愛丁堡學派形成于20世紀70年代英國愛丁堡大學的一批社會學和歷史學學者成立的“科學元勘小組”,小組成員基于默頓科學社會學的理論困境,決心以科學知識的內容與社會的關系作為自己的研究主題,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研究群體稱為愛丁堡學派。愛丁堡學派的代表人物有巴瑞?巴恩斯(Barry Barnes)、大衛?布魯爾(David Bloor)、史蒂文?夏平(Steven Shapin)以及安德魯?皮克林(Andrerw Piekering)等,愛丁堡學派受后庫恩科學社會學影響較深,該學派所關心的是:解釋信念或知識在一定的社會環境、歷史文化條件下,為什么得以產生或維持。曼海姆早在《意識形態和烏托邦》一書中就提出過這樣的思想:某些人相信某些信念是由社會因素決定的。但這種思想隨即出現了到底是“什么人相信?”和“何種信念有其社會根源?”的問題,因為傳統科學知識社會學長期以來把信念分成截然不同的兩種:一種是數學和自然科學,另一種包括宗教、道德、智慧等,前者被認為是質樸的,不為任何社會利益上的考慮所左右;而后者則是懷疑的,意識形態的,受主觀思想和利益驅動的,因而是社會的。正如當代杰出的知識社會學家斯塔克(Stark )認為的:“因為人們關于自然的事實是他發現的,而文化事實本身就是他自己的工作,這兩種情形中,知識的社會決定是不同的。庫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中對科學知識積累的解釋進行了批判,隨著科學知識的發展,大量的理論和原理被懷疑,并且成功被替代,庫恩認為這些不再是對增長的關于實在知識的簡單響應,而是用關于推理和評價的背景負荷才能表達的。既然自然科學和文化科學一樣,并非以純積累的方式變化,那么這是否意味著我們考察自然科學的產生及其維持一定要求助于社會原因呢?愛丁堡學派對此做出了肯定的回答。巴恩斯指出:“科學沒有任何特權,因為其信念與實在或理性有一致的相應關系,因而其文化傳播過程與其它領域所采取的相比,絕沒有更重要之處。也就是說,科學不應該被認為在認識上優于其它任何信念和知識體系,因此,對科學知識內容的解釋,就不能再囿于以往那種忽視和否認社會因素作用的解釋模式。
該學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布魯爾在其開創性的著作《知識及社會意向》中提出了“強綱領”( Strong Programme )(相對主義建構論方法的別稱),他認為:所有知識,不論是經驗科學知識還是數學知識,都應該對其進行徹底的研究……沒有什么特別的界線存在于科學知識之中,或存在于合理合法的真理及其客觀性的特殊本質之中。“強綱領”的“強”具體體現在它要公正地對待所有的信念體系,不論是真的還是假的,合理的還是不合理的,成功的還是不成功的,以使社會學方法能應用于描述一切知識體系,包括數學和邏輯學這樣遠離經驗的科學,開創了一種社會化認識論,堅決主張:科學地研究科學知識的性質。具體來說“強綱領”可以定義為以下四個信條,即(1)因果性。它應當是表達因果關系的,也就是說,它應當涉及那些導致信念或各種知識狀態的條件,當然,除了社會原因之外,還會存在其它的、將與社會原因共同導致信念的原因類型。(2)公正性。它應當對真理和謬誤保持客觀公正的態度,即都毫無例外地要求經驗調查并對它們產生的原因給予公正的說明。(3)對稱性。這是就其風格而言的,就是說,同一些原因類型應當既可以說明真實的信念,也可以說明虛假的信念。(4)反身性。這是就原則而言的,其各種說明模式必須能夠運用于科學知識社會學自身,和有關對稱性要求一樣,這種要求也是對人們尋求一般性說明的要求的反應,如果不是這樣,科學知識社會學就會成為一種長期存在的反駁其自身的理論。對于以上四條,要特別注意因果性中提到的其它原因,這些原因是指諸如精神的、人類學的、生理的、認知的和感覺經驗的等因素。愛丁堡學派認為由于在“實在”和我們對“實在”的陳述之間沒有任何內在的必然聯系,因而因果性也即意味著我們不可求助于那種在科學和自然現象之間預先設定聯系而排除其它可能原因的做法。公平性告訴我們對于進行科學知識的社會學研究沒有必要陷人“真理和理性究竟意味著什么”這類毫無意義的問題之中,這樣的問題對信息存在的解釋而言是多余的,毫無必要的。對稱性要求對于兩種不同的情況盡可能地運用同一種類型的說明,布魯爾打比方說:生理學的目標是說明健康的有機體和病態的有機體,機械學的目標是人們理解正在運轉的機器和出了毛病的機器、依然矗立的橋梁和已經倒塌的橋梁。反身性很明確,即科學知識社會學是其自身的原因,它自己首先要能夠合理地被解釋。“強綱領”在知識論的研究方面認為:“知識”是“任何被集體地接受的信念系統”。知識不僅包括傳統意義上的科學知識,而且還包括其它時代的文化中相當于科學知識作用的神話、魔法、宗教等各種信念系統,科學知識與其它信念系統具有同等的地位,因而也應該與其它知識系統一樣接受社會學方法的研究。
“強綱領”在真理觀的研究方面認為:所謂一個理論的真理性的確定,常常是在它被選擇并運用于實踐之后,在因果說明中逐漸反映出來的,即社會為獲得真理的心理體驗提供或強加了很多因素,因而社會因素也就成為真理的必不可少的成分,根本不存在真理符合論,真理與“實在”的一致性形式是多樣的,要想給真理下定義,最好是從真理的功用性著手,并且還把真理看作是一種文化符號,即關于“真”的信念是相對于特定社會和特定文化共同體而言的,不存在超歷史、超文化的真理標準,從而對科學的客觀性提出了自己的否定態度。
三、愛丁堡學派的“利益模式”
“利益”是愛丁堡學派的另一個重要概念。但是把“利益”引人對知識的社會學說明并不是愛丁堡學派的首創,早在19世紀,馬克思就采用了階級利益分析方法開展對政治經濟學的批判,馬克思斷言:一個時代統治階級的觀念,是受統治階級的利益決定的,并為統治階級的利益服務的意識形態,并提出了“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基本命題。馬克思認為,人類歷史是在客觀世界提供的自然環境中演進的,這個環境不斷地被人類的行動所改造,在改造的同時,人類創造出他們的生存方式,從創造活動中產生了社會關系,同時也創造了關于這個世界的知識,這些知識反映了各種社會群體的利益,并受到在當時特殊生產方式下盛行的意識形態的制約,它們既被用來操縱自然現象,又被用來支持或改造現存的社會關系。事實上,馬克思并未把科學與意識形態同等看待,他認為自然科學的關注焦點和發展速度或許為社會條件所決定,但科學的概念工具和實質結論卻并非如此。到了20世紀30年代,這一模式開始被用于對科學和知識的社會學研究,曼海姆深受馬克思的“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思想的影響,在他的兩部奠基性著作《認識論的結構分析》和《意識形態和烏托邦》中,曼海姆著重強調了知識與社會之間的互動關系,試圖用因果鏈將知識與外部世界聯系起來,認為知識就其社會學意義而言,不僅取決于人們的社會地位、身份及階級利益,而且扎根于特定的文化類型之中,并且肯定了利益是影響知識的一個因素。由于曼海姆是在對知識的二元劃分的基礎上談利益對知識的影響,所以是把自然科學排除在受利益因素影響之外的。默頓命題的第二條強調了經濟和軍事的功利性在科學組織化過程中的作用,似乎帶有一些階級利益的因素,但是默頓的科學社會學僅僅停留在對科學知識的產生做外部的說明,雖然有一些利益影響的因素,但其利益對科學的影響同樣不觸及科學知識的實際內容,只是對科學知識的關注焦點、課題方向以及特定領域的知識何以得到迅速增長的外部體制的說明。
愛丁堡學派使用“利益”的概念是為了解決強綱領中提到的“歸因問題”,按照強綱領的思路,科學知識與社會因素之間普遍存在著因果關系,如果用A代表某種社會因素,用B代表某個科學概念或理論,則A > B成立。愛丁堡學派認為巴恩斯所說的社會因素就是利益,即“思想或信念是否以及如何能被認為是社會階級或其他集團的特殊利益的結果”,可以使用“利益”作為一種解釋資源,對科學知識的擴展和應用及其與行動者的目標之間的關系進行社會學的因果說明。這些利益可以是社會體制上的或經濟體制上的,也可以是宗教上的或專業事務上的,有兩個案例可以用來說明利益理論:(1)巴恩斯列舉了20世紀生物學界在進化論觀點和遺傳觀點之間發生的一場激烈論戰,論戰的雙方分別是以卡爾?皮爾士為代表的生物統計學家和以威廉?巴特森為代表的“孟德爾主義者”。前者認為:生物繁衍是一種通過變異的連續選擇而進化的過程,這種過程是可以預知和控制的;后者則認為:生物的繁衍是一連串的突變過程,這個過程根本不可預知和控制。兩種觀點可以說是針鋒相對、截然相反。那么其根源何在呢?巴恩斯認為根源在于雙方的利益沖突,他認為,皮爾士的進化論觀點與新興的優生學密不可分,優生學主張通過逐步改變社會中不同人群的相對出生率來改善種族,其理論基礎是進化論,并且直接代表著新興中產階級的利益,是主張社會進步的。而巴特森之所以強調生物繁衍的不連續性和不可預知性,是因為他的立場保守,其階級利益依賴于傳統的社會秩序,害怕社會的進步,宣稱社會突變的時刻還沒有到來。(2)皮克林則利用職業利益來解釋一些學術之爭。他認為:對每一個科學家來說,都會存在一些更有利于其工作的資料、理論或模型,由于每一個科學家都在自己的專業領域投人了大量的時間,因而他們傾向于承認那些與自己的認識利益相吻合的新成果。如在分析萊夸克時,皮克林同樣使用“利益”分析工具,認為當時新發現的粒子在解釋上存在“色”和“味”之爭,而“味”能夠取得勝利,是因為對新粒子做“味”的解釋更符合主流傳統的利益,也更能體現權威物理學家在其中的影響等。
事實上,利益模式所要說明的重心不在于知識的真偽問題,不關心在被接受的理論中哪一種更能反映事實,哪些方面更合理,而只關心知識是否為科學共同體乃至整個社會所承認和接受,以及探討這種理論被這個階級承認和主動選擇接受的原因所在,由此得出:不同的利益決定不同的科學理論。也就是說,利益是分析知識狀況的必要因素而不是充分的因素,利益并不必然導致某種知識主張,但某種知識主張背后一定存在某些利益緣由。后來才逐步上升為利益是科學理論的決定性因素的。利益模式的出發點倒是可以接受的,而由此上升的夸大利益的決定作用則過于偏激,讓人難以接受,其實利益也像其它社會因素一樣,至多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在某些方面對科學知識的形成起到一定的干預作用。